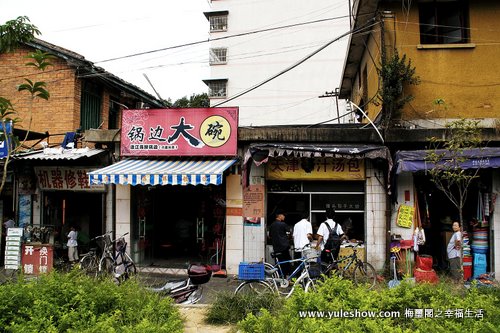Related Posts
福廈小吃之三 海蠣煎
2006年3月 廈門 許多網站上對廈門美食的介紹,第一個就是海蠣煎,都說怎麼怎麼好喫。然而看看照片,像隻雞蛋餅,看那些人的介紹,基本上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在我第一次到廈門時,就第一時間去了南海漁村。點了一份海蠣煎,一喫,發現原來是老朋友了。 海蠣煎是用海蠣做的,至於海蠣是什麼,對於上海人來說,要講清楚卻似易卻難,上海人也喫海蠣,不過另有名稱,叫做蠣黃。蠣黃燉蛋,是甬(寧波)裔上海人的日常小菜,這些蠣黃,以前是裝在木桶裡,現在是裝在塑料痛裡賣的。桶裡的東西可如一大團糨糊,有著許許多多半截小指大小的顆粒,還有澀白、粘稠的流體,那些小顆粒很像軟體動物,由於蠣黃是海裡來的,於是想像中應該有殼。 海裡有種東西叫牡蠣,會不會就是蠣黃呢?牡蠣剝出來的樣子和蠣黃很像,以至於我在很長的一短時間一直以為蠣黃就是牡蠣。牡蠣也叫蠔(蠔),很大,也很難剝,要用專門的工具和手法來橇開。在上海,一枚生耗要賣到十幾元,而且要到高檔的酒樓才見蹤影;而蠣黃剝好之後不過十幾元一斤,是不上臺面的東西,所以想來想去,應該不是同一樣東西。 海蠣應該不是什麼稀奇物事,沿海各地都有出產,記得有位瀋陽的朋友向我介紹大連方言時,就用「有股海蠣子味」也形容。我雖是「沿海」的上海人,但大多數其實都沒見過上海的海,所以更不知道這「象海蠣子味的大連話」到底是什麼味了。 言歸正傳,來說海蠣煎。海蠣煎往往在一個大煎鍋裡製作,就像上海做鍋貼、生煎的那種平底大鐵鍋,做海蠣煎其實用不著那麼大的鍋,所以攤主也衹是在鍋邊一隅放點油,等油熱了,攤主放下一些大蒜葉子翻炒,香味就騰起來了。然後攤主舀起一勺海蠣放在油上翻炒幾下,再舀起一勺早起加水調好的蕃薯粉漿澆在海蠣上,蕃薯粉遇熱凝固,就將海蠣粘成了一張餅狀。 攤主稍事煎烤後,將餅翻個面,繼續煎烤,隨手他又拿起一隻雞蛋來打散後淋在餅上,然後再翻過餅將蛋煎黃,海蠣煎就算做好了。聞著香,喫著更香,大蒜葉經過炒制不覺得沖,新鮮的海蠣且鮮且嫩,加之軟軟的粉晶瑩透亮,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搭配,以至於我每回到了廈門都要盡情的喫個夠。 這東西,看來衹要有原料做起來並不難啊。於是我每次回到上海,總要買了蠣黃,調好水澱粉,耐耐心心的做一回,可我每次都是真正做成了一張餅,不但硬而且脆,和廈門的軟綿綿的「正宗貨色」比起來,不衹是大相逕庭,簡直是天壤之別啊。 後來,請教高手總算弄明白了,原來我們上海的澱粉都是玉米澱粉,一經油煎立刻變硬,而廈門的用的是蕃薯粉,燒熟後依然是軟的,關鍵的區別就在於此。 廈門的海蠣煎大多用大蒜葉,也有用蔥的,據說是台灣的做法,我沒有喫過不敢枉加評論。其實我第一次喫這玩意是在新加坡,不過當時喫的時候店招上寫的是「蠔蚵煎」,所以在本文開頭中,我說這算是老朋友了。後來又聽廈門的朋友說在閩南話中,這東西就叫蠔蚵煎,可見的確是同一種東西了,一種東西叫兩種名字而已。 然而問題又來了,既然海蠣煎和蠔蚵煎是同一種東西,那麼蠔和海蠣到底劃不劃等號呢?聽一個朋友說,海蠣子的個頭很小,而牡蠣很大,這個疑問等下回再尋究竟吧。
[尋味LA]奧特萊斯國人多 華人照燒味道好-Sarku Japan, Ontario
現在,我正坐在Ontario Outlets的「大食代」裡,寫這篇文章;我知道,「大食代」是一個品牌,某個東南國家的品牌。上海最早的先買後端著自己找位子的食檔,就是「大食代」開的,所以打那以後,我管這種形式的food court一律叫「大食代」。 Ontario的這個奧特萊斯,是室內的,好像是加州還是全美最大的室內奧特萊斯;它是個巨大的建築,開著車遶著它走一圈,也得開一會呢。這個奧特萊斯總共有十個入口,於是華人圈裡親切地稱它為「十扇門」。 我剛從Coach裡逃了出來,所有的顧客都是中國人,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是衹買個皮夾或掛件的,每個人都拎著好幾個包,我算是見識到了。在這個奧特萊斯,我敢保證你每次都能看到中國孕婦,也保證可以看到坐在推車裡的中國寶寶;中國人週末很少去郊遊,有很大一部份中國人最愛做的,就是買東西。 我今天來,是為了二樣東西。第一我想要個手包,可以放一個小的筆記本,二個手機,一枝筆和幾張卡就可以了;對的,筆記本是可以放進手包的,不是因為我的筆記本新式,衹是因為我的筆記本是不用電的,它是紙做的小本子。 我還要買雙鞋,從我開始跑步至今,六年了,我一直穿Asics的,基本上每年換一雙,衹用於跑步,不穿著做其它的事。這不,前幾天發現去年的那雙裡面的幫上破了,打算週末來買雙新的。 對的,去年的那雙也是這裡買的,我還不知道洛杉磯其它還有哪裡可以買到Asics的鞋;雖然這裡有,但依然美中不足,美國沒有2E的鞋碼賣,就是腳掌比較寛的那種,我衹能加大半碼買普通款的。 為了一雙鞋就要跑次奧特萊斯,還是蠻興師動眾的,其實家人要去買別的東西,衹要叫她們帶買一下就行了,可我還是挺喜歡這家奧特萊斯的,所以就來了。 有人一定會問:居然有男人喜歡奧特萊斯?奧特萊斯應該設立男人寄存點才對! 我絕對同意這句話,大食代就是我的寄存點,food court is my destiny! 據說男人購物和女人是大同相同的,男人想好要買什麼,到了店中直奔主題,買了就走;而女人呢,到了商店中,要一家家地逛過去看過來,最後買了一大堆東西卻偏偏忘了去時要買的東西。這個說法在我們家基本成立,衹是不至於會把一開始想買的東西忘了。 問題來了,要是我們一家一起去奧特萊斯怎麼辦? 答案就是:把我自己寄放在大食代裡。她們去逛,我在大食代喫東西,寫文章,我的文章中,有好幾篇是我坐在這家的奧特萊斯的大食代寫的,還有更多的是在各種百貨公司的大食代寫的,或者裡面的咖啡館。 大家可能會猜想我每次到這裡的奧特萊斯,就在大食代喫不同的檔口,各種各樣的味道嚐過來。 然而,我並沒有,我很喜歡「十扇門」,雖然離家挺遠的,但我還是樂意開車過來,就是因為這裡的一家食檔。這裡的大食代,總共有Cinnabon、Stone Oven、Panda Express、 Chipotle、 Chicken Now、Kelly’s Cajun Grill、Charleys Philly Steaks、Burger King、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