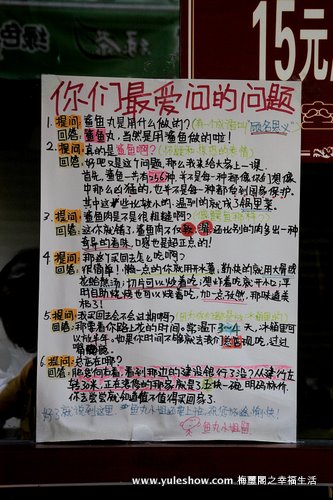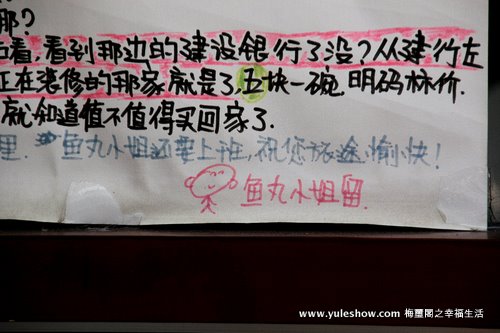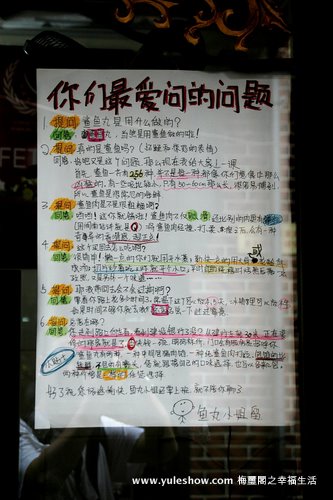Related Posts
小眼鏡大排檔
在「阿發」吃了一頓,上網查一下「醬油水」的來歷,於是在「點評網」找到了一家叫做「小眼鏡」排檔的地方,排在口味榜裡,排名還相當靠前。於是,中午打了個電話定座,對方聽我只有一個人,有點淡淡的,不肯定位,說什麼「到時來有位子的」,在我的堅持下,定了一個位。下午睡了一覺,醒來就叫車直奔「小眼鏡」。 「小眼鏡」在一條小路上,我大約是六點半到的,果然已是座無虛席,要不是定了位,肯定是吃不到的了。 依然是站著塑料筐前點菜,沒有看到土筍凍,於是隨便點了幾樣。網上說「蒸魷魚」是特色,就要求來一份;服務員問我要不要「海瓜子」,一看,就是我喜歡的「薄殼」,也要了一份;看到廚房的人拿了個燉盅,把蟶子一個個塞進去,覺得好玩,也要了一份;最後因為「阿發」的葉子魚好吃,就要求也來一份醬油水,服務員推薦了一種怪怪的魚,說是十五元四條。 依然沒有問價錢,網上說「小眼鏡」的價格低得離譜,這回我又帶足了錢,不怕。 這回,沒有沿街的位子給我坐了,從後面上樓,倒是有房間,一間四桌,還有空調,內帶衛生,算是很高的待遇了。 桌上擺著一碟黃豆,是送的,也是用肉燒出來的,但是味道沒有「阿發」送的花生好。 菜很快就上來了,蒸魷魚其實也是醬油水,魷魚很白,也很嫩,味道倒是還不錯。 等薄殼上來,興高采烈的挾起就吃,這玩意,上回在珠海吃了,唸唸不忘,又經《中國飯店美食之旅》的吳昌壽先生點撥,更是朝思暮想,不料在此撞見,當然要一飽口福。挾一起一堆往嘴裡塞,不料卻把我著實辣著了,這哪是廈門菜啊,上面堆著紅辣椒,辣味直衝喉嚨,嗆得我幾欲流淚。 仔細地看了一下,又試探性地挾盆邊的吃了幾個,發現盆邊的不辣,想必是炒好後,上面放蔥放辣椒,再用熱油淋的,於是挾起辣椒,再勻勻地拌了一下。再吃,果然味道好許多,醬油加糖炒的,有咸有甜。 味道雖然好了,東西卻還是不怎麼樣,關鍵在於「薄殼」太小了,沒有肉,炒呢,又稍微過頭了一點。也難怪,這麼小的薄殼,放在「砲臺」上炒,當然一入油就老了,細細想來,小眼鏡的便宜口碑不是沒有道理的,用料便宜了,價格當然就下來了。 蟶子,在網上見到有人稱之為「觀音舌」,這也未免太過份了吧?我一直覺得哪怕是「佛手瓜」,起得也有點過了,豈不料還有如此厲害的,不服不行啊! 插蟶,就是把蟶子豎地插在燉盅裡,然後蒸熟,燉盅裡會以有小半盅的湯,很是鮮美。不過,蟶子稍嫌瘦小,而且還有泥沙,這玩意看來很是簡單,不妨回家後,做一次試試。 最後的醬油水魚,端上來只有三條,說是「大的話,就是三條」,魚很乾瘦,遠沒有昨晚「阿發」的好吃…… 這頓飯,連一瓶「勁酒」總共55元,著實便宜得有些出乎意料,但從味道上講,如果阿發可以打到80分,那麼小眼鏡只有剛剛及格。 我有時在想,有句話叫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想添一句「盛名之下、何得至味」。 這個就是插蟶,蒸的,頂上有點幹了,我想不妨可以蓋上蓋子燉,或許可以好一點
福廈小吃之三 海蠣煎
2006年3月 廈門 許多網站上對廈門美食的介紹,第一個就是海蠣煎,都說怎麼怎麼好喫。然而看看照片,像隻雞蛋餅,看那些人的介紹,基本上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在我第一次到廈門時,就第一時間去了南海漁村。點了一份海蠣煎,一喫,發現原來是老朋友了。 海蠣煎是用海蠣做的,至於海蠣是什麼,對於上海人來說,要講清楚卻似易卻難,上海人也喫海蠣,不過另有名稱,叫做蠣黃。蠣黃燉蛋,是甬(寧波)裔上海人的日常小菜,這些蠣黃,以前是裝在木桶裡,現在是裝在塑料痛裡賣的。桶裡的東西可如一大團糨糊,有著許許多多半截小指大小的顆粒,還有澀白、粘稠的流體,那些小顆粒很像軟體動物,由於蠣黃是海裡來的,於是想像中應該有殼。 海裡有種東西叫牡蠣,會不會就是蠣黃呢?牡蠣剝出來的樣子和蠣黃很像,以至於我在很長的一短時間一直以為蠣黃就是牡蠣。牡蠣也叫蠔(蠔),很大,也很難剝,要用專門的工具和手法來橇開。在上海,一枚生耗要賣到十幾元,而且要到高檔的酒樓才見蹤影;而蠣黃剝好之後不過十幾元一斤,是不上臺面的東西,所以想來想去,應該不是同一樣東西。 海蠣應該不是什麼稀奇物事,沿海各地都有出產,記得有位瀋陽的朋友向我介紹大連方言時,就用「有股海蠣子味」也形容。我雖是「沿海」的上海人,但大多數其實都沒見過上海的海,所以更不知道這「象海蠣子味的大連話」到底是什麼味了。 言歸正傳,來說海蠣煎。海蠣煎往往在一個大煎鍋裡製作,就像上海做鍋貼、生煎的那種平底大鐵鍋,做海蠣煎其實用不著那麼大的鍋,所以攤主也衹是在鍋邊一隅放點油,等油熱了,攤主放下一些大蒜葉子翻炒,香味就騰起來了。然後攤主舀起一勺海蠣放在油上翻炒幾下,再舀起一勺早起加水調好的蕃薯粉漿澆在海蠣上,蕃薯粉遇熱凝固,就將海蠣粘成了一張餅狀。 攤主稍事煎烤後,將餅翻個面,繼續煎烤,隨手他又拿起一隻雞蛋來打散後淋在餅上,然後再翻過餅將蛋煎黃,海蠣煎就算做好了。聞著香,喫著更香,大蒜葉經過炒制不覺得沖,新鮮的海蠣且鮮且嫩,加之軟軟的粉晶瑩透亮,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搭配,以至於我每回到了廈門都要盡情的喫個夠。 這東西,看來衹要有原料做起來並不難啊。於是我每次回到上海,總要買了蠣黃,調好水澱粉,耐耐心心的做一回,可我每次都是真正做成了一張餅,不但硬而且脆,和廈門的軟綿綿的「正宗貨色」比起來,不衹是大相逕庭,簡直是天壤之別啊。 後來,請教高手總算弄明白了,原來我們上海的澱粉都是玉米澱粉,一經油煎立刻變硬,而廈門的用的是蕃薯粉,燒熟後依然是軟的,關鍵的區別就在於此。 廈門的海蠣煎大多用大蒜葉,也有用蔥的,據說是台灣的做法,我沒有喫過不敢枉加評論。其實我第一次喫這玩意是在新加坡,不過當時喫的時候店招上寫的是「蠔蚵煎」,所以在本文開頭中,我說這算是老朋友了。後來又聽廈門的朋友說在閩南話中,這東西就叫蠔蚵煎,可見的確是同一種東西了,一種東西叫兩種名字而已。 然而問題又來了,既然海蠣煎和蠔蚵煎是同一種東西,那麼蠔和海蠣到底劃不劃等號呢?聽一個朋友說,海蠣子的個頭很小,而牡蠣很大,這個疑問等下回再尋究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