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一路151號
2004年6月6日
No. 151 Ruijin Yi Road
June 6,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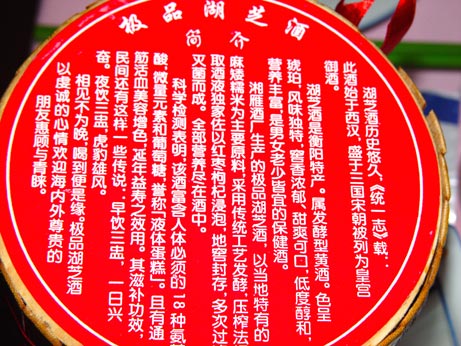

瑞金一路151號
2004年6月6日
No. 151 Ruijin Yi Road
June 6,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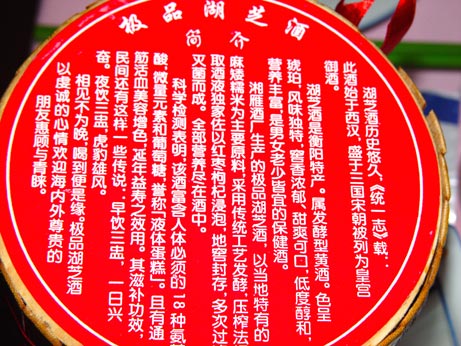

1993年的秋天,在天平路的一戶居民家中,一樓的大房間外是個小院子,小院子中有間搭出來的小屋。雖然已經秋天,但是小屋依然悶熱,沒有空調,衹有臺電風扇,但是一房間中好幾個男生,依然散發著燥熱,寫字桌前已經擠了二三個人,我衹能坐在床上,視線越過他們的頭,看著寫字檯上的電腦屏幕。 電腦的主機放在桌下,顯示器雖然衹有十四英吋,卻是個大傢伙,左右佔據了一半寫字桌,前後更是完全佔滿,鍵盤衹能放在拉出來的抽屜上,那種顯示器發熱很厲害,讓原本就逼仄的小屋更熱了。 電腦用的是Windows 3.1系統,英文版的,為了使用中文,要安裝一個叫做「中文之星」的軟件,中文之星是單向型的,裝上就卸不下來了,中文之星不但提供了中文環境,連電腦菜單都會變成中文的,我們當時覺得很神奇。 「吱吱吱」,愛普生針式打印機響著,很慢很慢,所以噪音響了許久,打印機的色帶被事先拿走,專門為了這個特殊的打印。最後,打印機終於吐出了一張半透明深藍色紙來,上面有著淡淡的白色字跡,深藍色紙下襯著一著薄薄的棉紙,再下面還有張格子紙。 「成功啦!成功啦!」 那是我們大學文學社第一次用電腦排版來製作蠟紙,在文學社成員學弟張睿無數次地試驗後,終於成功地打印到了蠟紙上。 等蠟紙打印好,我們小心地把它拿到了學校裡,千萬要小心,有一條摺痕壓痕印痕,最終印出來的東西,就會多一條莫名其妙的黑線出來。回到學校,我們拿出笨重的油印機,取掉笨重的蓋子,把蠟紙覆到黜黑的滾筒上,把一疊白紙鋪到一邊的進紙輪下面。 想想現在的激光打印機真是發達,快的一分鐘可以打幾十張,我們當時油印校刊,要用這個手搖的油印機,一張張搖出來,雖說進紙也是自動的,但是那個進紙輪很笨,每印一張,都要掀起面上的那張紙,把下面的紙壓住,否則,會一下子進個二張三張四張,都有可能,沒有定數。 先要一張張印出來,等油墨乾了,再印反面,等很多張都印好,還要裝訂,然後發給訂戶,說是訂戶,實際上是按班攤派的,倒是沒有靠學校的行政壓力,靠的是真誠和皮厚。 我們這樣的印法,其實已經是鳥槍換炮後的了,在這之前,我們是鐵筆手寫的蠟紙,手推油印出來,與我小學時的一樣。 時間閃回到1979年,那個後來變成21路終點站的平房,老師在刻蠟紙。 冬天,顧老師坐在辦公室裡,天已經很冷,她戴著半指絨線手套,還揣著熱水袋。她的面前擺放著一張蠟紙,蠟紙是透明的,下面印著橫線和竪線,組成了一個個一釐米見方的小格子,以便對齋。蠟紙的下面,是一塊木板,木板當中鑲著一塊薄的鐵板。所謂刻蠟紙,就是用鐵板墊著,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鐵筆是塑料的,衹是前端有一根鋼針,鋼汁並不是太尖,否則容易戳破蠟紙。 天冷,手卻不能焐得太熱,否則蠟紙上的蠟會化,化開的地方印出來,會有團黑影。油印的原理是用鐵筆書寫,寫過的地方蠟紙上的蠟被刮去,油墨就能滲透過去,留在紙上,「拷貝」出蠟筆相同的內容。 寫字,難免會有寫錯的時候,不要緊,有修改液,那是個玻璃的小瓶,瓶蓋上連著一把小刷子,把瓶蓋打開,小刷子上沾著塗改液,塗到要修改的地方,待乾了後可以再寫。 那時,是手推的油印機,說是機器,也就是個木框,木框靠近操作員的地方,當中有個把手。木框把蠟紙夾住,下面放紙,用一個與木框等寛的滾筒,蘸好了油黑,左手壓緊木框,右手捏住滾筒的把手用手往前推到底,然後拿起滾筒,掀開木框,下面就有張印好的紙了,對的,當時來說,就是考捲了。 那時,老師們很喜歡「差」學生做事,學生們也很喜歡幫老師做事,被「差」的學生,還頗有種榮譽感。唯獨這印考卷的事,雖說又髒又累,卻沒法讓學生來做,衹能親力親為。我依稀記得,等到了高年級,好像有過測驗卷子是同學幫忙刻的蠟紙,我們班有個「四條槓」的大隊長,是「紅領巾列車」的副列車長,不對,我們班有二個四條槓,是正副列車長,刻蠟紙的是那位副列車長,笑容甜美的顧錚鋒,也可能是「崢峰」。她有一個深深的酒窩,一笑就很甜,之所以我記得這清楚,是因為她寫過一篇作文,那篇作文成了範文,老師讀出來給全班聽,其中有個情節就是她曾經打算用筷子在另一邊臉上鑽個對稱的酒窩出來。 有些事不是記得太清了,可能卷子不是她刻的,那麼就是有通知是她刻的,等我們三年級搬到新校舍,那時不用老師自己印蠟紙了,那裡有專門的油印室,記得好像是在二樓,進門上樓轉角的地方。 蠟紙、油印,是七八十年代很普遍的一件事,各大工礦企業的通知,政府機關的文件,各種各樣的小規模宣傳品,都是用蠟紙和油印的,無外乎就是手推式油印機和手搖式的區別,但是製作蠟紙,還是好幾種的,手刻衹是其中一種,當時叫做「謄蠟紙」。 英文老師就不用謄蠟紙,他們可以用英文打字機,把色帶拿掉就可以打,不像後來我們用電腦打時,要買專門的打印蠟紙。不用英文老師也不能全用英文打字機,有時有「中翻英」的題目,還是要用到鐵板鐵筆。 大的單位,有中文打字機,好像我們中學就有,但那是印考卷的地方,學生是進不去的,要等到我大學畢業,進了單位,才得見盧山真面目。 說是打字機,與英文打字機幾十個鍵不同,中文打字機,衹有一個鍵,一個長長的鍵,鍵上有個把手,打的時候,要捏住整個把上,用力壓下去。中文打字機有個字盤,字盤中放著幾千個常用字,打字的時候,打字員坐得高高的,左手推動字盤,字盤可以前後左右移動,把要打的字移到那個把手相應的位置上,壓動手柄,就把擡起那個鉛字,打印到前面的滾筒上,滾筒裝上蠟紙,打出來的就可以油印了。 中文打字,是個高技術的體力活,要學習很久才能掌握,不僅要「對準」鉛字,還要背出字在字盤中位置,要牢記幾千個字的位置,據說字盤還能換,還有非常用字字盤。 還據說,中文打字機最早是林語堂發明的,沒想到吧,1946年!不過林語堂發明的不是這種死板的字盤式,而是一種基於字形的滾筒式字模打字機,鍵盤是類似英文打字機的六十四個鍵,每個字按三鍵,就能通過機械的方法在滾筒中的七千個字中找到相應的字,簡直可以說基於字形的中文輸入法,是林語堂發明的,用一種機械的方法完成了電腦的輸入法,他的那檯打字機,還可以整合部首,打出冷僻字,總供可以打出九萬個漢字來。後來到了1979年,還真有電腦公司買了林語堂的輸入法,起名「簡易輸入法」,不過衹在臺灣地區推廣,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由於我們的政府深知油印物的力量,當年的傳單就是手刻蠟紙,手推油印的,所以在我中小學那個時候,對於蠟紙的管控是很嚴格的。個人,是買不到蠟紙的,想買蠟紙,要有單位的介紹信,買來的蠟紙有專人保管,需要用的時候去領。領來之後,刻蠟紙也好,打蠟紙也好,都要有紀錄,不但如此,刻壞的蠟紙,還要還回去,不能有一張蠟紙流落在外。別說那個時候了,就是我們讀大學要印校刊的時候,依稀記得還是去學生處開了介紹信才買到的蠟紙,衹是買來後的管理沒有那麼嚴格了。 油印的卷子,是有油墨香氣的,哪怕做不出題,但香氣還是在的。我記得在高中後期,好像有些卷子就已經不是油印的了,而是複印的,但也可能記錯了,附近有個延中複印社,後來成了上市公司。反正,等我讀大學時,幾乎已經看不到油印的東西了,除了我們親手編的校刊,說是校刊,其實就是文學社的社刊,一份非法出版物,因為學校沒有校刊,我們就「僭越」成了校刊。
這些天,寫《上海回憶》,寫到了一些中學裡的事情,結果有很多同學校友找到了我,都說「你的記性怎麼那麼好?」。其實吧,就像我上一篇中說到的,我是個內向的人,內向的人與人交流少,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時間來冷眼旁觀物和事。 我想,我的小學體育老師肯定不會同意的,前幾天,我們小學同學建了個群,體育老師說:「我記得你,你從小就喜歡和老師聊天、軋山湖。」所以,還好我與人交流少,要是多的話,估計老師都沒上課的機會了,都得聽我說。 其實我的記性也不是那麼好啦,比如說,初中的事,以「班級」這個單位的記憶就有些模糊了。好在,高中的班級,我記得很清楚。 高三有四個班級,一班白痴班,二班流氓班,三班革命班,四班掃盲班;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這幾個詞語的描述實在是「穏准狠」。有趣的是,這幾個綽號被全校接受,哪怕是白痴班和流氓班的同學,也照樣認可。 白痴班的存在,實在是沒什麼存在的意義。一班學習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課外活動不是最好的,同樣不是最差的;下課打球,他們永遠不會贏,但也不至於墊底;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都沒有他們班的事,與其它幾班風起雲湧、驚濤駭浪相比,他們始終就是個死水微瀾的狀態,老師永遠都不會用一班舉例子,永 遠不會說一班有個誰誰誰怎麼怎麼樣。學校裡好像就沒有這個班似的,甚至被叫做「白痴班」時,他們也沒有太大的反應,沒打算改個名字什麼的。 二班流氓班,就是我所在的班級,那時我們絲毫沒有為名字而忤,甚至覺得「流氓」二字帶著某種程度的「俠氣」,先不說二班,我們聊下去。 三班革命班,那是個很有趣的名字,在一個早「忘了」「革命傳統」的年代,居然有一個班被叫做了革命班,有一整個班的革命小將,真是有趣。那時,七一中學,有各種各樣的活動,黑板報比賽,詩朗誦比賽,三班永遠是最積極的,只要有三班參加的集體比賽,大家爭的就是第二名了。 記得有過一次歌詠比賽,在比賽前的二個月,三班每天下課後都留在教室裡排練,他們弄得很神秘,每天排練都把前後門關得緊緊的,還有人察看窗外有沒有人偷看偷聽。 那次歌詠比賽是在學校西北角的一個大倉庫舉行的,全校廿四個班級,記得好像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那天,三班好像是唱了三個歌曲,其中一個是小組唱,還有一個是《畢業歌》,三聲部還是四聲部的合唱,我也不懂,只知道那種唱法很不簡單,因為別的班級都是一個聲音的大合唱,而三班的《畢業歌》是有高有低不一樣的聲音,甚至各個聲部之間的唱詞也是不一樣的。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我們真是被他們唱得「熱血澎湃,鬥志昂揚」,心想著該如何地報效祖國。沒有了啦,真要這麼寫,就不是閣主的寫法了,高三的我們,剛經歷了那個多事之秋,充滿了迷惘和困惑,我們看不到歌中「起來」的可能,那時的我們,有能力的想著出國,沒能力的等著高考,渾渾噩噩,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的。 說起那次的歌詠比賽,我們班著實是沒有任何準備,等到要比賽了,班主任桑玉梅先生來問我們打算怎麼辦,我們如實回答:「不知道!」,流氓班嘛,事情做不好,豪氣還是要有的。 好在桑先師急中生智,給我們臨時抱了佛腳,不至於叫到班名時來個「棄權」,她教我們唱了《團結就是力量》。前面說到,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所以等我們一上台,一報歌曲,下面就響起了笑聲。然而,作為出盡風頭的二班,會隨大眾、和大流嗎?當然不會,我們的第一句就和別人不一樣。 傳統的《團結就是力量》第一句就是歌名「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唱的就不是,我們的多了二個字:「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第二句,和第一句一樣;第三句,和第二句一樣,也就是說和第一句也一樣;換言之,我們把一句話唱了三遍。 接著是第四句,和前三句不一樣了,先是一個字,「嗨!」,記得好像還一起跺了個腳,然後是唱詞:「團結就是力量!」 第五句,哪來的第五句啊?!在聽眾們聽到又有一首《團結就是力量》時開始笑,當他們還沒笑完的時候,我們已經紛紛跳下台了,有些人甚至開了個小差都沒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多年以後,有人學我們當年的做派,搞出一種活動來,叫做「快閃」。 再來說四班,四班為什麼叫掃盲班呢?話說四班是全高三成績最好的,好像不管什麼樣的考試,年級排名前幾十的都是四班的,除了我班有位老兄獨得總分第一之外,從第二到第四十,好像是四班獨攬的,也就是說剩下的三個班級是在搶四十名以後的名次。 放學以後,一班肯定是沒人的,他們放學就走,二班肯定是有人的,一半左右的人,而三班四班是全班留在教室的,三班唱歌做節目,四班自習做卷子。四班的人,永遠都在學習,我們說他們就像是海綿吸水似的在學習。誰最想學習?誰學習最認真?當然是文盲啦!文盲一旦有了讀書認字的機會,哪個會不珍惜?那四班這種自發的學習熱情,非「文盲」二字莫屬了。 好了,剩下二班了,流氓班,真的流氓嗎?在北京話中,「耍流氓」指的是性侵女性,好在我們全是上海學生,整個流氓班,沒有耍過流氓。 先說一個故事吧,有一次開校會,我不是說過嗎?校會課,是大家輪的,其中有一個年級是在階梯教室中,現場聆聽校長和教導主任的訓話,其它的班級在教室裡聽廣播。那一次,我們高三「有幸」輪上,都去了階梯教室。 那次校會,校長和教導主任各拿了一隻面盆去,及其正式校會,老金頭把面盆從台下拿到台上,說:「這是我們從高三收來的撲克牌,這是從一個班級收來的一部撲克牌!」,老金頭說得義憤填膺,大力拍著桌子。老金頭說話有二個毛病,一是喜歡噴唾沬,同學們經常開玩笑說坐在前排要撐洋傘,另外老金頭說話一急,就會有大量的口水湧出來,積在嘴角的二邊,很是滑稽。 印象中,好像不僅是學生,哪怕是老師也挺怕老金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核的學生的同時,也做著考核老師的工作,教導主任,可能放在大學裡,就是黨委書記了吧?那倒真的是挺厲害的,哎,話說當年的老師們,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想到來和同學聯手的呢? 當年的老師太天真了,當然,可能現在的我更天真。…
2004年6月26日 紅松路168號 喬老爺茶餐廳 第一次去喬老爺茶餐廳,是因為好友楊軍要敲我「竹槓」,我讓他選店,他就選了這家。家面不大,進深也小,我就詫異楊軍是否故意要為我省錢。當時,喫了點啥,幾乎全忘了,只記得楊軍極力推薦了一套餛飩,說是如何如何的好。那家店並不怎麼合我的口味,倒不是「喬老爺」不合口味,而是茶餐廳這種形式。因為酒喝不盡興;菜呢,雖說不貴,但量也是很大;加之座位侷促,不如在大飯店裡的感覺好。然而,這家「喬老爺」如果和一般的街邊小店比,這裡乾淨、明亮,算得上是很好的店裡,的確,和香港的那些茶餐廳比起來,這個算是很好的了,雖然味道不一定比得上。 第二次去,還是和楊軍,這回還有他的女友和我們夫人、孩子。喫的還是餛飩,我總算喫出裡的蝦來了,那天他們還推薦了章魚丸和煲仔飯,味道都相當不錯,丸子很有彈性;煲仔飯呢,很香。 喫了兩次,我並沒覺得好,當然,也沒覺得什麼不好,可偏偏夫人喜歡上這家店了,只過了一個星期,就嚷著想喫,於是,特地打了車過去,只剩一張桌子了,欣然就座。可能是餓了的緣故,這回喫得感覺不錯,我們點了兩種丸子,一份餛飩,一份臘味煲仔飯,一飯蝦仁滑蛋,另外還有三隻蛋撻,三隻菠蘿包和兩瓶啤酒,總價 119 元,可謂物美價廉。 丸子,是該點的特色,有魚丸、章魚丸、牛肉丸、牛筋丸和蝦球,那些丸子個頭挺大,做得極有彈性,喫口很好,碗裡有湯有生菜,一份五到六隻丸子,售價十幾元。 餛飩也是一碗五隻,十五元,不像上海餛飩是包起來的,倒有點象燕皮餛飩般捏成的,裡面有蝦有肉,也帶著極好的彈性。 我最喜歡的是煲仔飯,喬老爺煲仔飯 18 元,臘味煲仔飯 22 元,要等二十分鐘。一個帶柄的砂鍋,燒得極熱,裡面盛著飯,上面蓋著甘蘭、香腸與其它物事,上桌之前,備有醬湯一壺,供以任意調味。當醬油澆入飯裡,遇熱發出滋滋的響聲,香氣撲來,食慾大開。由於砂鍋燒得很燙,因此,飯始終是熱的,如果一個人去,喫上一份,便可裹腹了。 這家的菜,大多十幾二十元,以清爽可口為特色,最適宜三四好友小聚,到了夏天,他們還會在街上擺幾張桌子,看看街景也不錯。

閣主,你這個……這個……像是單位裡婦女節組織活動啊
悄悄說:「閣主夫人最漂亮,^**^
知道湘園搬到哪裡去了嗎?今年十月去找竟然發現不見了!
關於涼皮,我覺得徐家匯鴻基休閒廣場裡的博望坡還行,但要提醒師傅別放太多鹽,還有一個就是老壇貴州菜裡的麻辣米皮。就大館子而言,這兩家算做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