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26日 紅松路168號 喬老爺茶餐廳 第一次去喬老爺茶餐廳,是因為好友楊軍要敲我「竹槓」,我讓他選店,他就選了這家。家面不大,進深也小,我就詫異楊軍是否故意要為我省錢。當時,喫了點啥,幾乎全忘了,只記得楊軍極力推薦了一套餛飩,說是如何如何的好。那家店並不怎麼合我的口味,倒不是「喬老爺」不合口味,而是茶餐廳這種形式。因為酒喝不盡興;菜呢,雖說不貴,但量也是很大;加之座位侷促,不如在大飯店裡的感覺好。然而,這家「喬老爺」如果和一般的街邊小店比,這裡乾淨、明亮,算得上是很好的店裡,的確,和香港的那些茶餐廳比起來,這個算是很好的了,雖然味道不一定比得上。 第二次去,還是和楊軍,這回還有他的女友和我們夫人、孩子。喫的還是餛飩,我總算喫出裡的蝦來了,那天他們還推薦了章魚丸和煲仔飯,味道都相當不錯,丸子很有彈性;煲仔飯呢,很香。 喫了兩次,我並沒覺得好,當然,也沒覺得什麼不好,可偏偏夫人喜歡上這家店了,只過了一個星期,就嚷著想喫,於是,特地打了車過去,只剩一張桌子了,欣然就座。可能是餓了的緣故,這回喫得感覺不錯,我們點了兩種丸子,一份餛飩,一份臘味煲仔飯,一飯蝦仁滑蛋,另外還有三隻蛋撻,三隻菠蘿包和兩瓶啤酒,總價 119 元,可謂物美價廉。 丸子,是該點的特色,有魚丸、章魚丸、牛肉丸、牛筋丸和蝦球,那些丸子個頭挺大,做得極有彈性,喫口很好,碗裡有湯有生菜,一份五到六隻丸子,售價十幾元。 餛飩也是一碗五隻,十五元,不像上海餛飩是包起來的,倒有點象燕皮餛飩般捏成的,裡面有蝦有肉,也帶著極好的彈性。 我最喜歡的是煲仔飯,喬老爺煲仔飯 18 元,臘味煲仔飯 22 元,要等二十分鐘。一個帶柄的砂鍋,燒得極熱,裡面盛著飯,上面蓋著甘蘭、香腸與其它物事,上桌之前,備有醬湯一壺,供以任意調味。當醬油澆入飯裡,遇熱發出滋滋的響聲,香氣撲來,食慾大開。由於砂鍋燒得很燙,因此,飯始終是熱的,如果一個人去,喫上一份,便可裹腹了。 這家的菜,大多十幾二十元,以清爽可口為特色,最適宜三四好友小聚,到了夏天,他們還會在街上擺幾張桌子,看看街景也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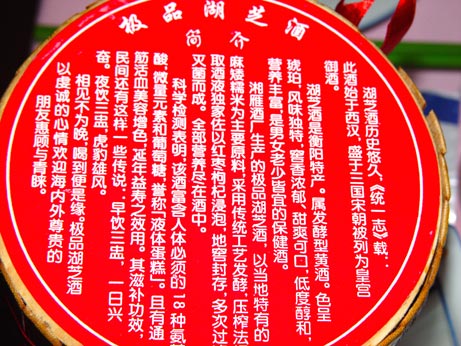

閣主,你這個……這個……像是單位裡婦女節組織活動啊
悄悄說:「閣主夫人最漂亮,^**^
知道湘園搬到哪裡去了嗎?今年十月去找竟然發現不見了!
關於涼皮,我覺得徐家匯鴻基休閒廣場裡的博望坡還行,但要提醒師傅別放太多鹽,還有一個就是老壇貴州菜裡的麻辣米皮。就大館子而言,這兩家算做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