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我有一個朋友,為人不錯,只是有一樁毛病,為人慳吝非常,不僅從來不肯從手裡「滑出一隻角子」,就是要他請別人吃頓飯麼,也比登天還難。不料此人,除此之外,還有一樁毛病,就是別人請客,他是「逢請必到」,甚至「不請自到」,只要有吃,必定能夠看得到他。 恰恰我是個好請客的人,就算沒有什麼喜慶,也要想著辦法,聚聚朋友,請請客。於是一來一去,我請他吃了無數次席,他卻一次也沒請過我,時間長了,大家發現這位朋友除了「吃」之外,倒也沒有別的惡習。大家混得熟了,也經常拿他開玩笑,開玩笑要他請客,他當然是不肯的。於是,有好事者就替我打起抱不平來,說他吃了我這麼多頓,為何一次也不肯「回請」,不料這位老兄「面皮老老」說「伊請我麼,伊自家情願呵,生得就是伊前世裡欠我呵,要伊今世來還呵。」 各位看官,你們說我冤枉不冤枉,明明請人吃了無數頓飯,還說是我「前世裡」欠他的,這「前世裡欠呵」,一來沒有借據、欠條,二來又沒有中人、擔保,所以總歸是個無稽之談,他算是訛定我了。不過,「前世裡欠呵」倒也是上海人常說的俚語,大凡說一個人,待另一個人太好,前者好得不得了,而後者卻偏偏不記他的情,不賞他的臉,別人就說前者是「前世裡欠的」。總有許多男人追女人,那女人不甚好看,然而男人愛得非常,雖然噓寒問暖、體貼非常,卻總是不得一親芳澤,這個男人就是「前世裡欠呵」了。反過來也是,女人嫁了個男人,那男人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在外姘相好,在家打老婆,不料那女人還是死心塌地跟著男人,為他衣食解憂,這樣的女人,也是前世裡欠了這個男人。 更有一種,生了孩子,從小不學好,書又讀不進,倒是闖出許多禍來,待得大了,也不尋工作,整天靠著爹娘生活,生活富裕的還好,更有生活拮据的,老人的退休工資不夠他揮霍,到老了反而要尋工作來「供養」這不肖子,這樣的大人,真正是「前世裡」欠著這小王八蛋了。你說男女之間,還有看穿、看破、看透的一天,只要把「前世的債」還清即可,而父子、母女一層,卻是萬萬還不清的了,但凡像這種情況,人們說「前世裡欠呵」時候,總不免帶著無限的感慨。 上海話中,「前世裡」是經常用到的,有時,並不用「欠」。比如說,有人做了某事,特別不上檯面,別人聽說了,就會說「真真前世是呵」,或是簡單為「前世是」。這句話,表達的一種感嘆,感嘆「怎麼會如此呢?」、「從來沒有碰到過」;既然「今生今世沒碰到過」,那麼當然要追溯到前世才有機會碰到了。 不僅是做事上不檯面,但凡奇事怪事,都可以用「前世裡」來表達感慨。比如有的人,吃相特別難看,坐在檯面上,狼吞虎嚥,所謂「眼光象霍顯、筷子像雨點,牙齒象夾鉗」,就是指的這種人,如此的餓急象,恐怕是「前世裡沒有吃過」。這句話,實則是說他乃是餓鬼投胎。再如有些人,不會打扮,卻又好出風頭,於是絲棉毛皮,全都穿在一起,金銀銅鐵,一併戴起,更是五顏六色,好似要把一家一當全都穿戴起來,可以送他一句「前世裡沒著過」,乃是窮鬼投胎的意思。 好了,既然說到「投胎」,不妨也來嘮叨兩句。投胎,是民間的說法,標準宗教上的稱呼是「輪迴」,佛教認為有六個平行世界存在,稱之為「六道」,也有說法是五個,叫做「五趣」。這些平行世界同時存在,人死後,依然會在這些平行世界出現,至於在哪個平時世界出現,就要看人的修行了。這些平行世界,有三個公認的「壞」世界,是「地獄道」、「餓鬼道」和「畜牲道」。地獄道,就是十八層地獄啦;照裡說,地獄裡的都是鬼吧,可不盡然,專門有一個道是給鬼的,而且是餓鬼;至於畜牲道,就是除了人以外,所有會動的動物,包括牛羊魚豬,一概歸為此道。 剩下的三道,有一個叫做「阿修羅道」,是最有爭議的,因為阿修羅們都很漂亮,但是脾氣暴躁,而且喜歡打架,不但喜歡打架,更喜歡打仗,所以人們並不想成為阿修羅。這樣一來,只剩下兩種了,就是「天道」和「人道」,「天」就是天堂,天堂裡住的,是佛、菩薩、仙人,然而對於凡人來說,天堂並不是任何人都可能去的,中國人向來不奢求,人們想要的,只是來世還可以為人,能夠為人,已經上上大吉了;當然,就像祥林嫂一樣,女人們都希望來世能夠變成男人。 所以,人們只剩下唯一的目標,就是來世還要做人,投胎的時候,要「投人身」。上海話裡,就有「投人身」一詞,專門指人心急慌晃忙 ,辦事急躁。說到這裡,我想到一個香港電腦,徐克拍的動畫片《小倩》,戲中寧采臣和小倩要去「投人身」,還帶著一隻叫做「情比金堅」的小狗,以及小狗的女朋友,他們去「投人身」的時候,拚命地往人道的那扇門跑,不但他們,無數的人,無數的牛羊雞鴨 ,一起往那扇門奔跑,彷彿恐怕跑得慢了,便投不成人身了,那架勢,倒像另一部動畫片《獅子王》中的動物狂奔一般。 於是我在想,上海的「投人身」一詞,或許也是事出有因的,是不是在「投人身」的時候,每次都是有名額的,非要跑得快,才能拿到那個名額,跑得慢的,就要等到下趟了。如此說來,「投人身」是一定要跑要趕的。 我們在路上,經常看到有種人,車子開得飛快,自行車騎得飛快,往往險象環生,路人看到了,就是「搿個人哪能介急呵,阿是要去投人身啊?」,過去有人誤解為「投人身」是「尋死」的意思,因為要先死了成鬼才能「投人身」,其實不然;實際上,但凡「投人身」的都是鬼,而且都是「急煞鬼」,乃是罵人為鬼也。 (寫於2006年7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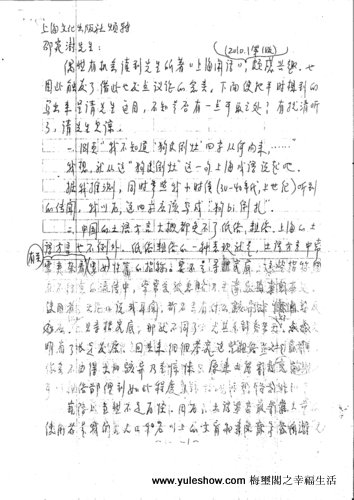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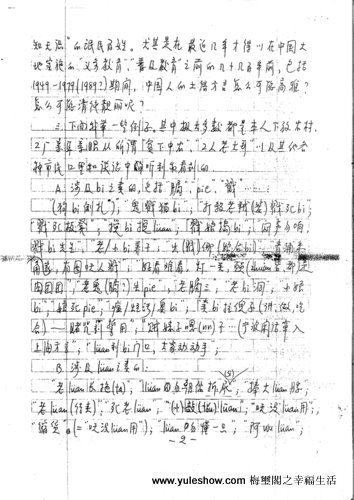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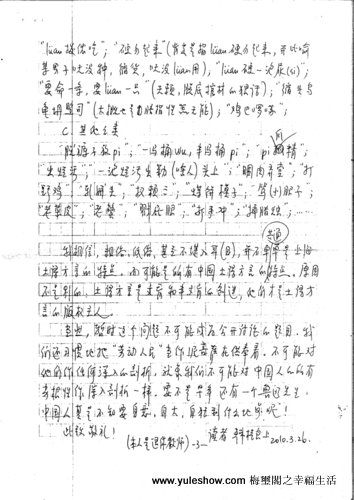
說滬罵大全沒有人會看?記得好些年前在餐館打工時見到廚師有本黃霑的不文集,雖不是集廣東粗口之大成,卻也令講廣東話的大開眼界,由於當時忙碌,只翻了一兩頁,前幾天幾位朋友又講卻此書,說己再版了60多次了。而今想買還得等些時日再版了。
我在這裡也要慫恿閣主一次了。
賈植芳先生在提籃橋監獄遇到邵洵美。邵懇求他將來出來的話,幫他澄清一件事。1933蕭伯納來上海,是他出錢做東的。蕭不吃葷,他就在南京路『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花了46塊銀圓。但是後來寫蕭伯納來上海,吃飯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林語堂……就是沒有寫他。
邵先生,你好!我是《LOHAS》雜誌的美食欄目編輯vivi,最近我在做一個關於粽子的選題,然後碰巧有一個剛讀過你的《下廚記》的朋友向我推薦了你的博客,讀下來我覺得你對食物有著非常獨特的認識和感情深厚的心得體會,因此想問問看你是否願意接受我們雜誌的採訪?由於在網站上找不到任何你的聯繫信息,只得在此給你留言,盼盡快答覆:)我的郵箱是:mynamy@gmail.com,希望能夠有機會進一步溝通,謝謝!
去年年底美國這邊出了一本書叫「Niubi!: The Real Chinese You Were Never Taught in School」,介紹當前中國各類粗話俗語行話流行語,現在反響不錯。
http://www.amazon.com/Niubi-Chinese-Never-Taught-School/dp/0452295564/ref=sr_1_1?ie=UTF8&s=books&qid=1273760191&sr=8-1
存在必合理。粗口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有雅言所無法代替的功用。就像北京陰三兒IN3說的,「這些詞不是語言,而是語氣」。
在下對粗口也很感興趣,以後還望多多交流!
劉津
上了你的當了,特地購了黃霑《不文集》來,首先不是粗口,其次不是廣東話,根本就是本黃色笑話集,不過倒是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