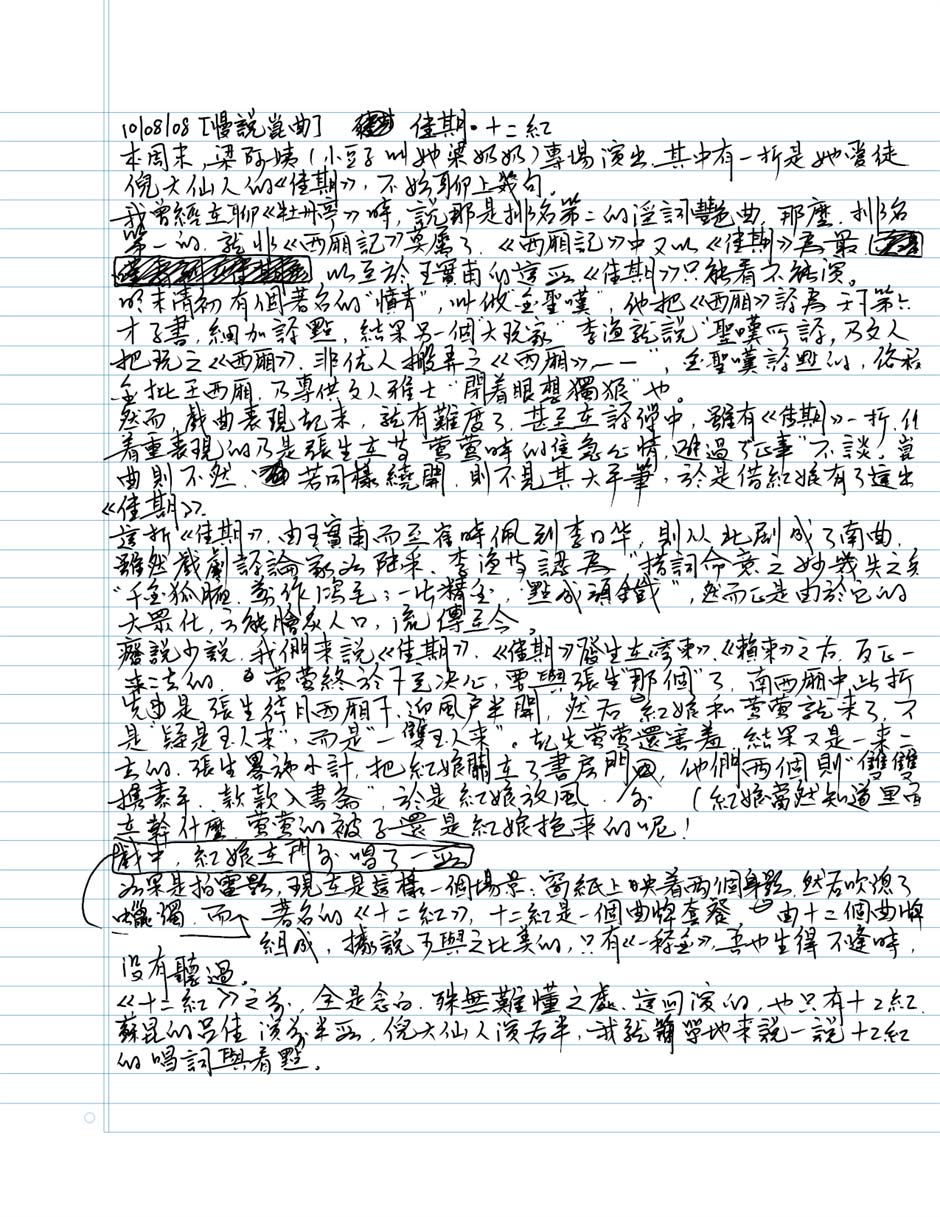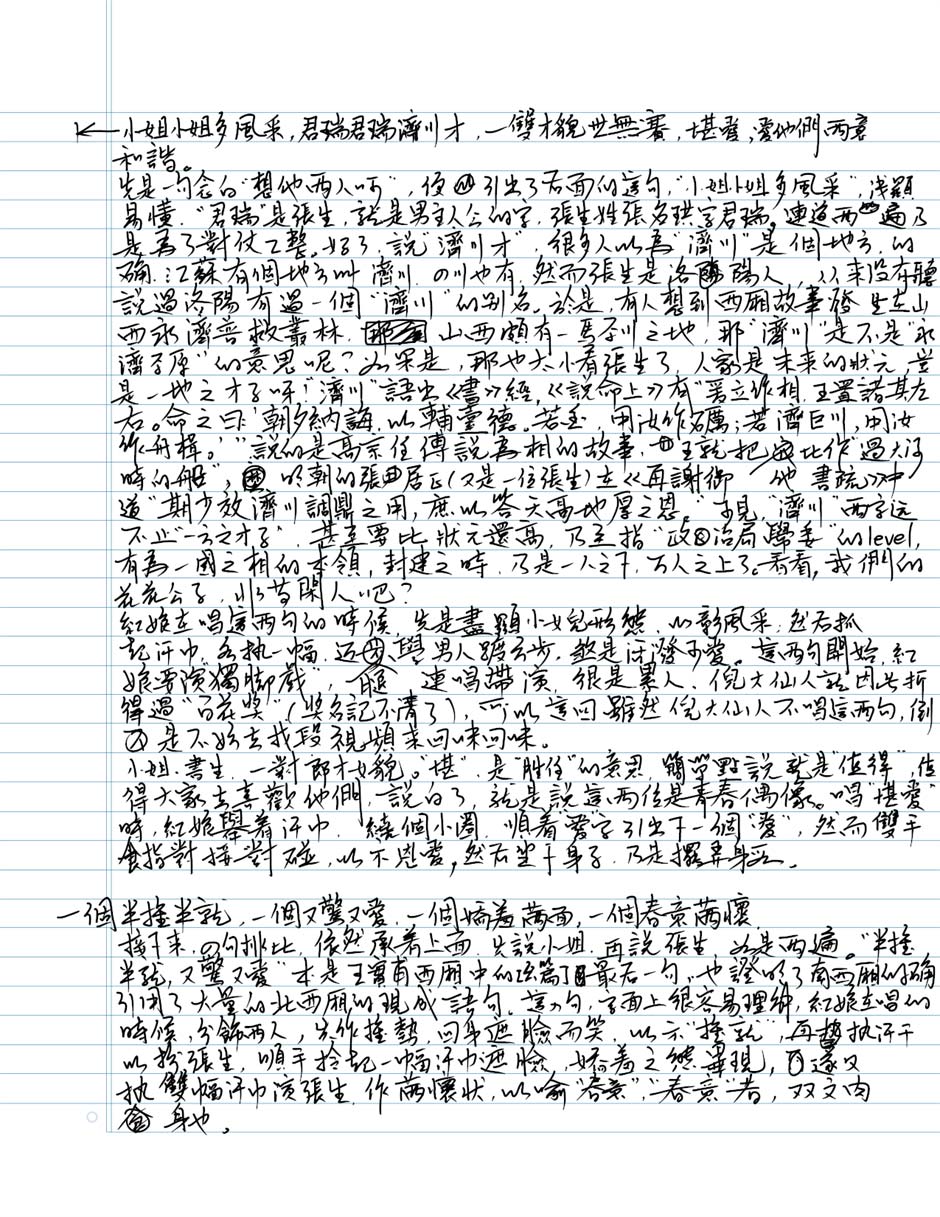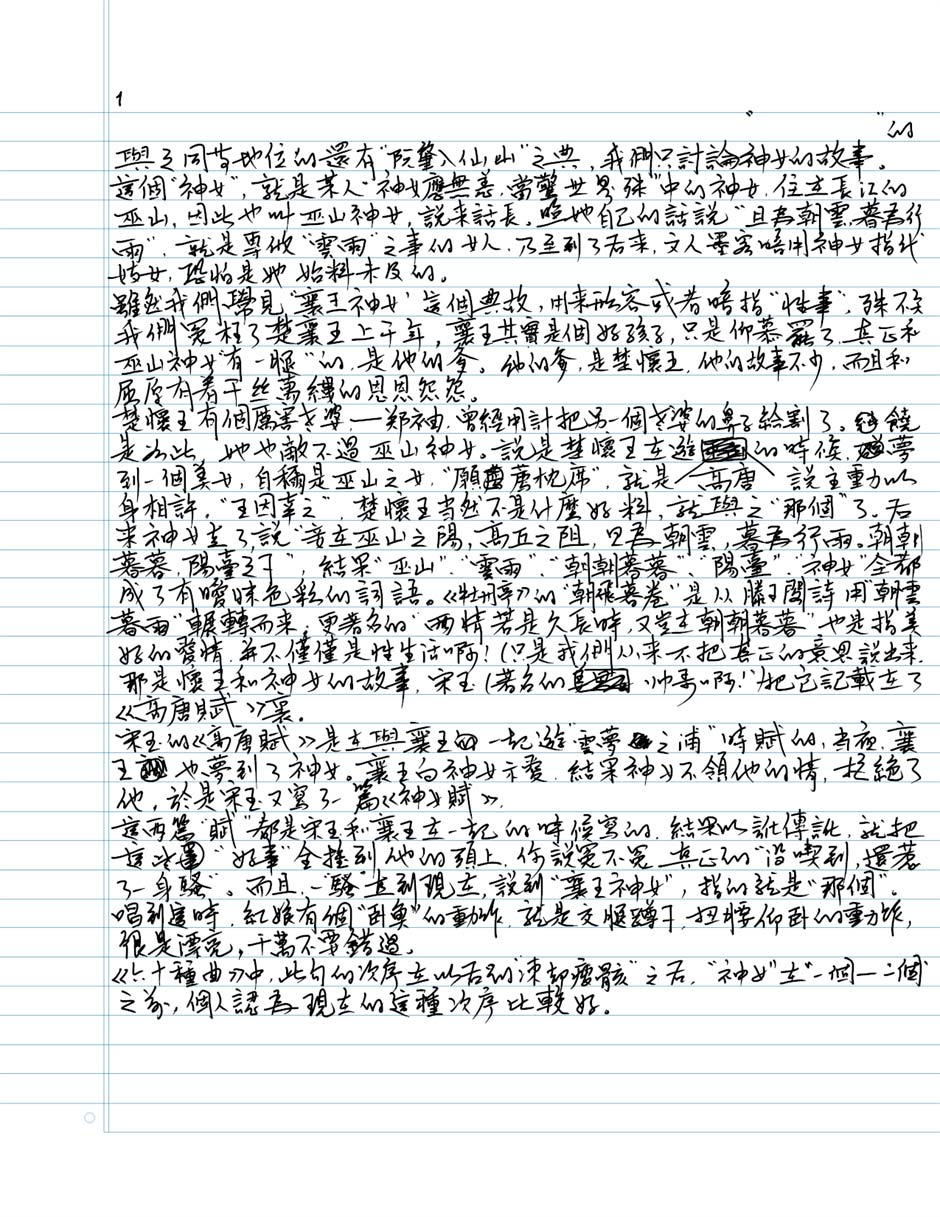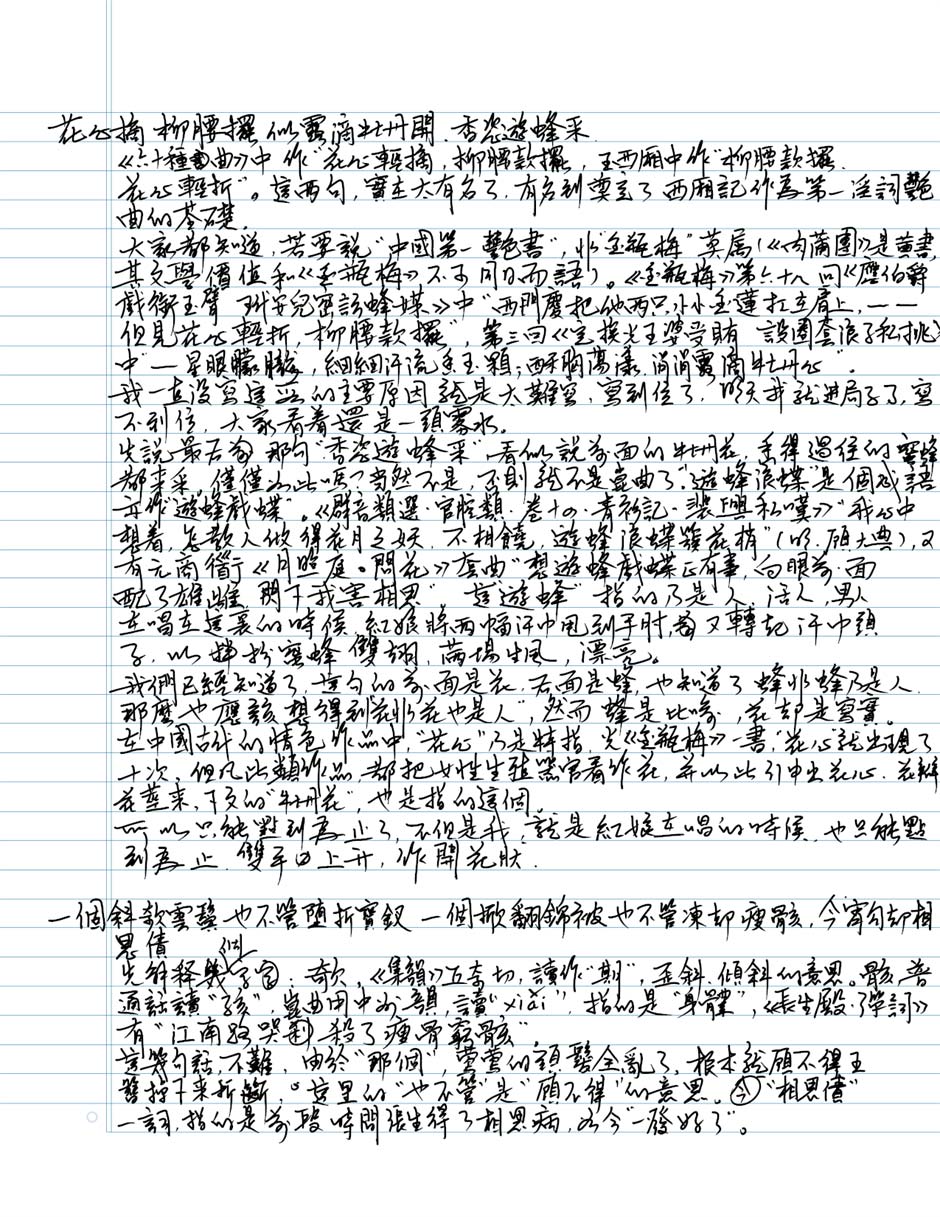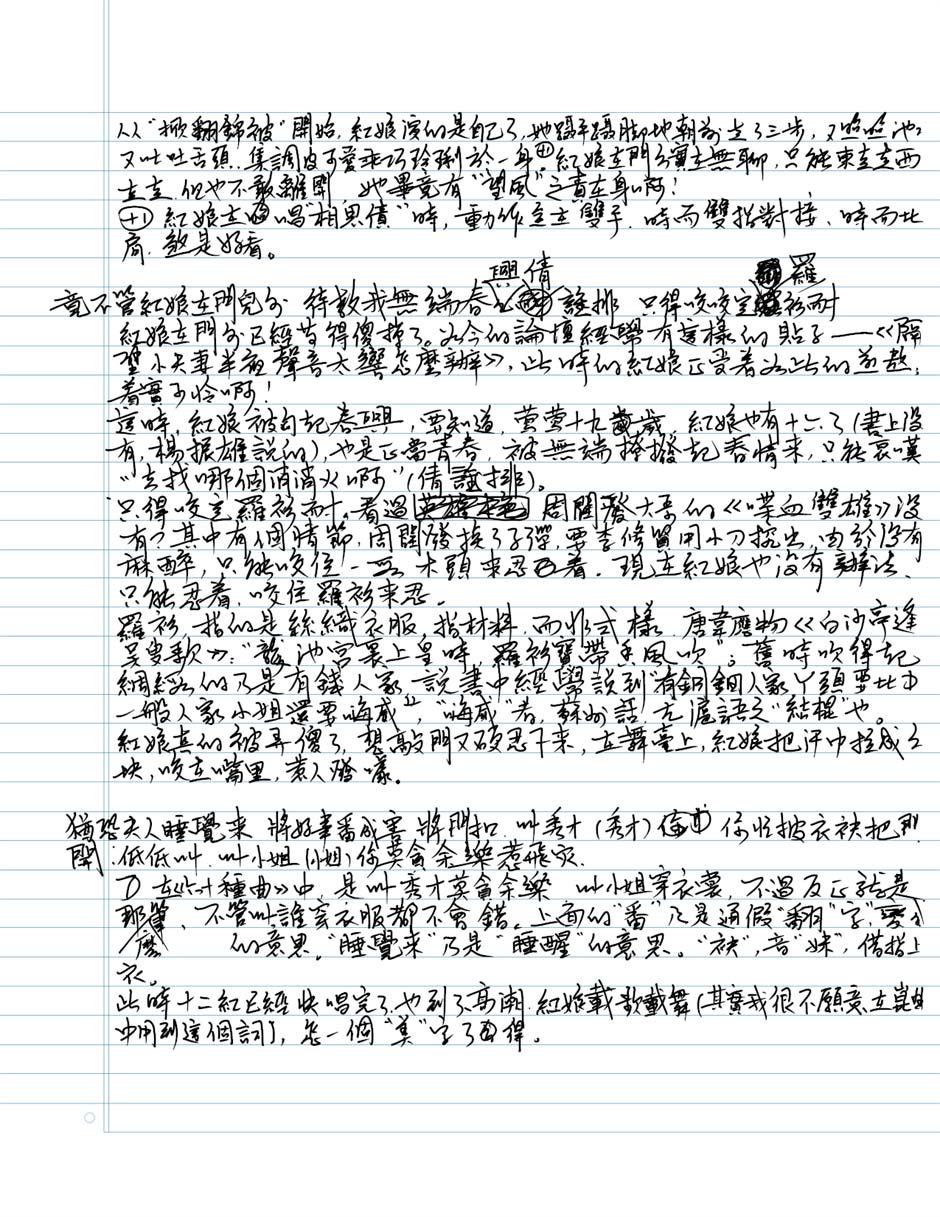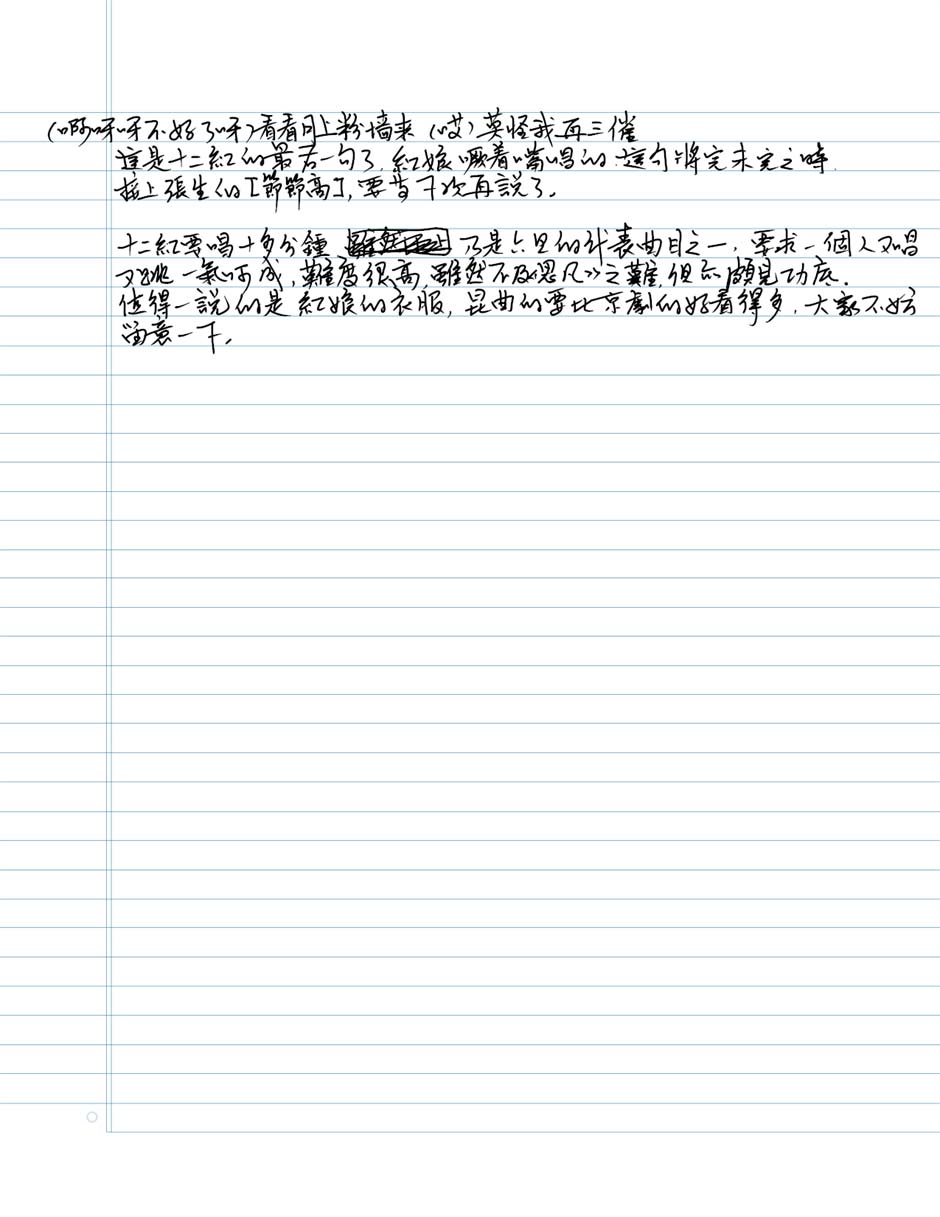大家知道,老蔡下來了,據說上昆新的團長是SMG派來的,這位老兄,看來要在崑曲史上寫一筆了。上面的圖,是最新的票折最右邊的特寫,設計者故意把這幾個字露在票折最顯眼的地方,告訴大家崑曲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戲劇。我想,這樣的票折拿在手裡,若是給不懂戲的家長、朋友、同事、同學看到,是不是會讓人嚇一跳,甚至於背後說”諾,誰誰誰就是喜歡崑曲的呀!那個崑曲喔……”(兩人交頭接耳狀) 不但如此,昆團最近有”七夕”的演出,最新的廣告詞如下: 求愛秘籍《佔花魁》癩蛤蟆垂涎天鵝的成功案例 戀愛寶典《風箏誤》古代愛情見光死的青春喜劇 忠愛真經《牆頭馬上》閃婚不誤終身事的典範之作 真可謂”譁眾取寵”的巔峰之作,據說為了此事,在百花園論壇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了,一吵文案,二吵票價。 新人一來,票價是明顯地上去了,我估計他們不打算走”戲迷”路線了,他們可能打算走”白領”乃至”洋人”路線。想想也是,我們這幫子人,週六下午小劇場花20元看一下午戲,看一場還要賣一場。人家洋人在新天地,花1000元看一場,還不覺得貴,看完了,肯定一口一個wonderful,一口一個magnificent,讓人聽著就開心。換了你是演員,你願意演給”戲迷”看,還是演給”白領”、”洋人”看? 或許,可以和旅行社聯合一起搞,第一天下午城隍廟,晚上浦江夜遊,第二天下午購物,晚上新天地,看崑曲,第三天……,這樣或許雙贏,也可以展示上海,估計昆團的新領導有此心思。 最近,芷江夢工場還有場《傷逝》,那裡的環境更符合昆團的新路線。 反正,能看的戲估計越來越少了,至少看得起的戲是肯定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