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2年8月18日
地點:上海書展上海熱線現場演播室
語言:上海話
主持人:付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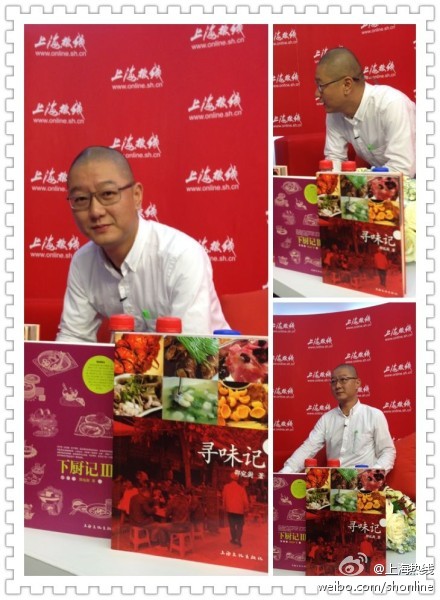
時間:2012年8月18日
地點:上海書展上海熱線現場演播室
語言:上海話
主持人:付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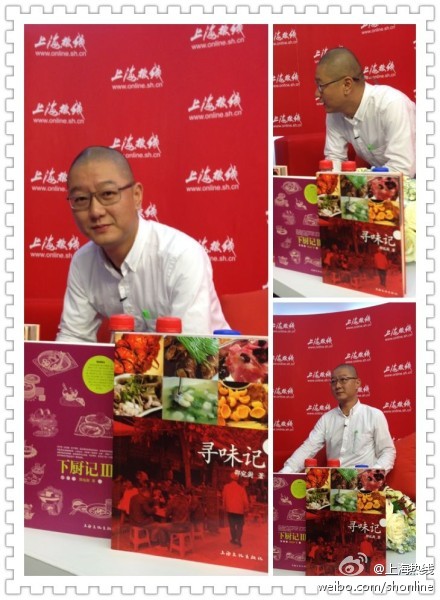
我有位朋友,相當有趣的一個朋友,我經常打趣地稱他「美食原教旨主義者」或者是「廚房原教旨主義者」,在他的眼裡,烹調的技藝、菜餚的形狀、味道的搭配,都要符合標準,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嘛!我的這位朋友認為老師傅傳下來的一定是有道理的,至於是什麼道理,老師傅沒說,於是這位朋友就從食物材料學、烹飪技藝學以及化學、物理的各個方法,去尋找答案,還真被他找出了很多的道道來。他認為一道菜,該切多長多短,該燒多熱多久,都是有標準的,他甚至還配合有關部門,給本幫菜製定了一個標準,符合這套標準流程的,才是正宗本幫菜,就如同給本幫菜弄了個ISO 9000。 我和他說「你那套是衹針對飯店的,不是尋常人家的做菜法」,他對我說「我又沒說過不是針對飯店,我尋求的就是有傳承的老飯店的頂級廚師的做法」,好吧,我們是二個流派的。 我一向是這麼認為的:衹要不冠以地名也不加上「正宗」二字,其實怎麼好喫比如何標準重要得多。你要說「正宗上海紅燒肉」,那一定不能放大蒜,《舌尖》有一季不正因為有外來人員在上海的租住屋中做紅燒肉加了大蒜而引起了軒然大波麼?其實,片中還沒說那是「正宗上海紅燒肉」呢!要我說,碰上特別有地域特徵的食物,加上一句「非標準」就行了,非標準過橋米線、非標準煎餅果子、非標準肉夾饃,先堵上「業餘廚房原教旨主義者」的嘴,然後再來討論怎麼做到好喫!說「業餘廚房原教旨主義者」是為了和我的那位朋友區分開來,我認為他是專業的,他說的是飯店,飯店賣的蛋炒飯不能放老乾媽,至於你家裡做,想放什麼放什麼,這是有很大區別的。 我有一次去臺北,住在一個叫做怡亨(Éclat)的酒店,酒店出門一轉彎,就看到一家老老舊舊的小店,一開間的門面,寫著「十八年老店赤肉羹‧魷魚羹老店」。一般形容小店小攤,經常有人會寫「髒髒破破」的,但這家店既不髒也不破,可哪怕它不寫「十八年老店」,也看得出應該開了很久了,墻紙發黃,排風扇的漆掉了,裡面的鐵已經生了鏽。 十八年?中華民國十八年?這家店老雖老,但說開了近百年,我是不信的。那是開了十八年的老店?難道去年十七,明年十九,還要年年換招牌?看那招牌,也不像是今年新換的呀?問了老闆娘,她說這家店在十來年前開了十八年,那一年的確換過店招,打那以後再也沒換過。 聽著好有道理! 後來我又發現好些鋪子都是「十八年老鋪」、「十八年老店」,甚至還有手推排檔車是「十八年老攤」,我猜可能「十八年」是個虛數,表示多的意思吧?「九者,數之極大也」,二個九,總夠老了吧? 那家店的羹,很好喫,鮮、香、熱、辣,我去的時候十一月,已經頗冷,一碗下肚,薄薄地出了一身細汗,很是舒服。以至於多年過去,我還惦記著那碗羹,總想著自己也做一回喫喫。 所謂羹,有二種,一種是用澱粉勾芡的湯,另一種,是物料本身就能稠厚的湯。羹,不是什麼太稀奇的東西,上海人常喫的薺菜肉絲豆腐羹,雪菜黃魚羹,都是羹;而羊羹,就是把羊肉燉到發黏發稠,以至於冷卻後可以凍結成塊,至於栗羊羹,是在真的羊羹的基礎上「發明」出來的一種用豆子葛粉等做成的甜品了。羹的歷史很悠久,最晚到唐朝就有了,當時的習俗,新婦過門三天後,就要「洗手作羹湯」來孝敬公公婆婆;至於到了宋朝,更有一道「宋嫂魚羹」流傳至今,當然也有可能衹是託名罷了。 焿,說白了,就是羹,但同時也是個地方特色的寫法,如同「餈」字到了上海就要寫成「粢」、「腐乳」也要寫成「乳腐」那樣,是一種特色。焿,好像衹有閩南文化中才有用到,說的就是羹,而且是「肉羹」。注意,「肉羹」是「有肉的羹」,不是「衹有肉的羹」。 一般來說,焿,要有一個好的底湯,哪怕雪菜黃魚羹,也不是純用清水就成的,要麼用雞湯,要麼用魚骨魚肉湯。什麼?你就把黃魚煎一下放水煮到湯白下鹹菜?那是大湯黃魚不是雪菜黃魚羹,後者魚肉是片下來的,沒有魚骨頭的。什麼東西都要有個好湯底的,哪怕就是個麻辣燙,哪怕就是碗小餛飩。 臺灣的焿,湯底用柴魚片燉煮,應該是受了日本的影響,海峽對面的閩南地區,就用肉湯、骨湯、雞湯。在調味方面,也有二種,一種加入沙茶醬一種不加,前者味型較重但可去腥添味,是個不錯的選擇;而後者,常用重白胡椒,與糊辣湯其實是一個路子,衹是羹裡的東西不一樣,嚴格地說,上海的酸辣湯,也是一種羹。 肉焿,有二種做法,一種是成條的肉,一種是肉糜,攪打後做成細條,不管是那種,都要裹上生粉,為的是表面的滑爽感。臺灣用以勾芡的生粉和大陸用的不同,大陸用玉米澱粉而臺灣用土豆澱粉,二者都是用水拌勻後倒入熱湯,但前者待冷卻後依然稠厚而後者冷卻後會「澥」掉變回湯而非羹。 焿中可以放各種各樣的東西,有的地方放胡蘿蔔絲,有的地方放金針菇,也有加入韭黃的,都可以,反正所有的輔料,都衹是為了減少主料的用量,並沒有什麼大的講究。我個人覺得,在江南地區,放入茭白絲,就是一種很好的改良。 主料,才是最重要的;肉,和魷魚,和蝦,和各種優質蛋白質,都可以做為主料,但除了魷魚章魚之外,一般都要「上漿」,也就是前面說到的「裹上生粉」,生粉要裹,但不宜厚,過厚口感不佳。 廈門也有肉羹,就對岸嘛,豬肉羹、牛肉羹、海鮮羹,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麵線糊和鴨肉粥,也是一種羹。羹,就是勾了芡的湯,既然湯裡可以有各種東西,那羹裡當然也可以有,不過我很難想像把老鴨芋艿湯或者醃(火篤)鮮勾個芡會是什麼樣子。 好吧,說了這麼多,我也來做一個吧,非標準魷魚焿,主料是金錢魷魚乾、章魚乾和肉糜。 魷魚乾、章魚乾都要發,最簡單的當然是清水浸發,但是單純用水浸發的話,魚身不會變厚,喫起來有老柴的感覺,而且純用水浸發時發有很多氣泡產生,過半天水就混濁了,應該是發生了些類似於發酵的變化。照理呢,是用食用鹼來發製的,我手邊沒有,好在我用的是金錢魷魚乾不過半個手掌大小,就用小蘇打,也行。美國的小蘇打幾美元一大袋,十幾磅,很便宜,平時但凡洗個沾了油的東西,都用它。 在容器中放入小蘇打,很多的小蘇打,放入魷魚乾和章魚乾,倒入開水,蓋沒為止,這時會有很多泡沫起來,不用管它。過一二個小時,水冷了,容器底部還有許多沒有溶解的小蘇打,可見這是小蘇打的飽和溶液了。潷去冷水,加入熱水,如是來個二到三次,魷魚乾和章魚乾會變厚至三到四倍,捏上去明顯有彈性,就算發好了。 把發好的魷魚和章魚表面的黑膜剝去,很容易剝的,魷魚上面還有二片小三角,撕下後也要剝去表面的黑衣。有人說我喫到的魷魚焿是不剝黑膜的,是的,那是攤主偷懶,自己喫,還是精緻點吧。魷魚的骨頭是一片薄薄的透明片,長長細細扁扁的,棄之;章魚身上、腳上的黑膜也要剝去,變成雪白的,才好看。 把魷魚和章魚切成手指寛的條,放在清水中浸泡,換幾次水,有趣的是,水中不再有氣泡,也不會變混濁了。 事先準備一小碗土豆澱粉,加一倍的水,攪勻後靜置待用。 肉糜,加鹽攪打上勁,然後用筷子刮成長條狀,在土豆澱粉中輕輕滾一下,大概二兩不到的肉,做成了八九條小肉條。 湯底,用的是清雞湯,加鹽加了點啤酒,燒開後,放入肉條,然後再放入切好漂洗好的魷魚乾和章魚乾。接著從浸著的澱粉碗中,用手抓起底部的沉澱的生粉,轉圈淋入湯中,然後再次攪勻生粉碗,分幾次倒入湯中,邊倒邊攪,直到湯明顯稠厚起來。 撒上大量的白胡椒粉,就可以喫了。一嚐,味道還真不錯,鮮、香、熱、辣,和我喫到過的十八年魷魚羹有得一比。什麼?我忘了說輔料?我壓根沒放啊!家裡自己喫,又是個「非標」的,我費什麼心思去弄輔料呀,主料多喫點,才過癮,我用了八個金錢魷魚乾和一個中等體型的章魚乾,真的很香,很有特色。 下回,做個鰻魚焿吧,也好喫,也有些小訣竅,可以和大家分享。
前段時間寫了篇文章,是關於上海菜為什麼「做不過」雲南菜的,結果又引起了爭議,我一向否認我是個「美食作家」,因為我也寫別的,但不妨認為我是個「爭議作家」,因為不管我寫什麼,美食也好,文化也好,語言、戲劇評論,都會引起爭議。 我常說「如果一個人看不慣你,那是別人的問題;要是一群人看不慣你,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了。」昨天,有人在周彤的美食群勸他不要得罪人,我接口到我可能是在美食圈中得罪人最多的了,一位朋友問我「你開始反思了?」 我的回答是:我的確反思了,而且我一直在反思,反思的結果是我並不後悔得罪了那些人。 是的,有一群人看不慣我,我也反思了,但我有更多的人喜歡我,看書的銷量和重印再版次數就可以了。因此,我至少還將我行我素一段時間。 說回上海菜,前面說到的那篇文章出去後,被人教訓了一頓,那人告訴我「本幫菜」早己沒落,根本不能代表「上海菜」,那些到了上海之後,在上海改良並發展的菜式,在上海落葉生根成為上海特色的菜餚,應該叫做「海派菜」,那些才是「海派菜」。 關於第一點,我是很同意「海派菜」的定義的,但凡現在衹有在上海有卻找不到出處的,或者找得到源頭卻已經和「原版」大相逕庭的,都可以稱為「海派」。別的不說,就是《下廚記》系列中,出現了多少「海派」啊?海派炸豬排、海派酸辣湯、海派鹽烤蟹,多了,是的,對我來說,是上海常見外地少有而本幫菜不見的,都可以加上「海派」二字,海派是沒有規則可循的,是衹講好喫不論傳承的,至於能不能代表「上海菜」我不知道,但的確能體現出上海持續發展的風範來,我以後多用用這個詞。 海派白斬雞?那本幫菜中就沒有了?有!本幫菜的雞,有人說要切得方方正正,所謂「割不正不食」,但我總是存疑,一個以會洋涇濱商業英語為榮的萬國碼頭,真的會奉孔學儒家為圭臬嗎?我想不會,我在別的文章中寫過,當時物質不像現在這麼豐富,邊角料是後廚的福利。 海派白斬雞的代表,是小紹興,你看,紹興人在上海做的在原地找不到的,就是海派,正看「嵊泗派杭州小籠包」一樣,你在杭州找不到。 小紹興的白斬雞,曾經被認為是上海最好喫的白斬雞,一到逢年過節是要排隊的;小紹興的雞是明檔現切的,客人就看著廚師切雞,於是也就沒有「福利」了,是整雞切塊裝盤的。其實,經驗豐富的廚師,就算當著客人面,也是能夠「平地摳餅,對面拿賊」的,各行各業都有秘密的絕活,廚師就有這本事;注意,我可沒說小紹興的師傅會短斤缺兩哦,在此聲明,不負任何刑事、民事責任。 小紹興的雞用的是浦東三黃雞,你說要是一個日本廚師專門在上海用法國食材做給美國人喫,那能不能算海派呢?或許也能算!但白斬雞,就是紹興人(最早)用上海食材做給上海人喫的,所以能叫「海派」。 浦東三黃雞,要嘴黃、皮黃、腳黃,也有說「毛黃」的,那是個誤解,過去我們買雞,都是活的,要把毛翻起來看毛下的皮是不是黃的。浦東三黃雞,有種自小被閹割的公雞,可以長得很大的卻依然很嫩,個中極品有長到九斤的,俗稱「浦東九斤黃」。閹雞在上海話中叫做「驐雞」,這個是正字,有的地方也用其異體字「鐓」,都發「蹲」的音。 浦東三黃雞很好喫,又香又嫩,香是雞特有的香味,嫩是入口無渣;然而浦東三黃雞的確不能算全中國最好喫的喫,我去過廣東喫了清遠雞後,才知道真的「雞外有雞」。再後來,光到廣東就喫過不下七八種雞,真是「一雞更有一雞妙」啊! 說回海派白斬雞,用浦東驐雞做,不在上海的話,可以選用大隻且嫩的雞,驐雞當然最好,我在洛杉磯買到一種三黃雞,冰鮮的,十塊九毛九,很好;洛杉磯也有活雞檔,衹是他們不能活的賣給你,必須替你弄好了才能帶回家,那兒有活的三黃雞賣,原料不是問題。 海派白斬雞,是用煮的,網上有說蒸的,大多數人家沒那麼大的鍋吧?蒸的話,溫度太高,皮容易破,雖然不會「外焦裡嫩」,但的確容易裡面溫差太大而造成口感不佳。 把雞買來,洗淨,特別是「夾肝」要摘去,頭不要了,如果沒人喫雞屁股的話,也剪了吧。找一口大鍋,放入整雞,放水蓋過,稍微沒有蓋過低一點也行,放入一塊拍碎的薑,一把打成結的蔥,然後加一點黃酒,用冷水開大火加蓋燒。 有二大流派,一種是水開後繼續燒煮五六分鐘至十來分鐘不等,燒完後立刻出鍋的;還有一種是水開後煮二三分鐘關火,再燜上廿卅分鐘的。 各有千秋!為了保持皮脆,出鍋之後,要把雞浸到冰水中浸泡,溫差越大越脆,燒煮的時間越短越脆,所以前者可以使雞皮更脆;然而這個方法,如果不是很有經驗的話,靠近骨頭的肉有時會有一點點生,而後者,基本可以避免。 一般認為,最好喫的白斬雞,是骨肉分離而切開的骨頭還是紅色的,這時的雞是剛斷生卻又最嫩的。這是傳統認識,但是萬一在禽流感疫情期內,千萬不要這麼做,性命要緊,就算不死為了個雞生場大病也不值,是不是? 雞要在冰水中泡透,切起來才不會散,趁這個機會,做個蘸汁出來,海派白斬雞是靈魂是蘸汁,沒有這個蘸汁,就不能稱之為海派白斬雞。 海派白斬雞的蘸汁,要蒸過,也就是說是熟醬油,但可以去看所有的菜譜,大多數也都會說要蒸過,但沒有一個是像我這樣配的,我可以保證你很好喫,可以保證你配出來之後會發現「哦,原來就是差了這麼一點點啊?!」 取一個碗,放一點熱水,然後是糖,再是生抽,放在鍋中大火蒸十五分鐘。生醬油有「火氣」,蒸熟是為了去掉這個火氣。大多數菜譜說要放雞精,這年頭的醬油中大多數都有增鮮劑,別再放雞精了。 切一小塊薑,切到極細的茸為止,但不建議用工具擦茸,那樣薑汁會有損失。切幾根蔥,主要是蔥白,也切到象薑這麼細,把蔥末和薑末拌在一起,一比一的樣子。 有的朋友喜歡放香菜,我不喜歡,也沒啥正宗不正宗的,香菜是在改革開放後才出現在上海菜場的東西,其味霸道,所以不合我意,這也是我現在燒紅燒肉不放冰糖的原因。 還有樣東西,速溶咖啡,沒想到吧?一點點,小半調羹的樣子,要聞得出香味,喫不出苦味,或許間有隱隱約約一絲絲的苦味即可。最後,淋上麻油,麻油一定不能多,很多朋友以為麻油越多越香,其實麻油一多,蘸汁就粘不上雞塊了,一滴滴地放,讓麻油的平面擴展開來,佔據蘸汁表面的五分之四左右的樣子。 把雞從冰水中拿出來,瀝乾或擦乾,然後刷上一層素油,隨便玉米油、茶樹油、精製油都可以,不要有香味的油,不要麻油,那樣會蓋住雞本來的香味,不要。 把雞肚子朝下頭朝前放在砧板上,直著將雞一剖為二,刀要夠快,要是不夠快的話也要果斷地一刀剁下,即使剁不斷,不要把刀拿起來再剁第二下,而是要右手捏緊刀柄,用左手掌根敲擊刀根,就是靠近刀柄的部位,直到把雞剁開。不熟練的朋友甚至每一刀都可以這麼切,怕自己對不準剁歪的話,就先把刀放在位置上,然後再用左手敲;左手的著力點,需要是掌緣肉最厚的地方,位置不對的話,特別要是靠近骨頭的話,會弄破手的,各位朋友,千萬小心。 把雞對剖下,割下翅膀和雞腿,然後把半爿雞拍拍扁,依然直放,再一剖為二,然後把二條雞橫放,剁成等寛的塊,一塊塊地剁,剁好後把刀平地塞入雞塊之下,把整盤移到盆中,另一條也是這麼操作,另一爿同樣如此操作。 等雞碼好,把雞翅和雞腿同樣剁塊碼在盆中,切雞腿前也要用力把雞腿拍扁,那樣和刀鋒的接觸面積最大,最容易切。 然後呢,就喫吧,店家的話,會在頂上放一根香菜,為了「好看好看」,在家如果沒有香菜,也不必強求。 最後,再說一句,在上海在北京,那些上海菜「做不過」的雲南菜,都不是雲南人經營的,那是資本的運作,為什麼資本沒有選中上海話來運作,那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地方。…
青海,回民筵席中有一道名菜,叫做「清蒸牛蹄筋」,是將牛筋帶皮一起烹製的,嫩香而不膩,極具高原特色,當地俗語有云:「牛蹄筋,味道賽過鮮海參」,可見牛筋之妙處。 至於這牛筋和海參,本是風馬牛不相及,誰知一入了菜,不僅可以相提並論,還能燒在一起,做成美味佳餚。過去,牛筋、海參、花膠等,還被併稱為「山珍海味」呢。 天漸漸地冷了起來,中國人向有「冬令進補」以及「藥補不如食補」的說法,這牛筋便是食補佳才。所費不多,味道鮮美,又可健腰膝、長足力,烹調也方便,何樂而不為呢?據說掉牛筋還有養顏美容的功效呢。 牛筋的營養相當均衡,其中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各佔三分之一左右,因此喫口相當好,又香又嫩,還有彈性,肥而不膩,乃是牛中珍品,與牛百頁及牛腦髓成為「牛中三寶」。 西北草原,牛羊眾多,這牛筋也不算是什麼稀罕之物,當地多半是加重料燉煮,蔥、薑、蒜、辣乃是特色。南方人,特別是蘇滬一帶,不太習慣;於是應運而生了這京蔥牛筋煲。 上海人,以豬肉為主,鮮食牛羊,因此牛筋也成了炙手可熱的好東西。這京蔥牛筋煲,質地滑糯、味厚醇和,看上去晶瑩剔透,煞是引人口水。牛筋煲需要長時間烹調,料又難弄,因此好多飯店也衹是「有名無菜」,只在菜單上列一條罷了;若是某店能做此菜,也一定要趕早或是提早預訂,因為一晚也就能提供幾份而已。 上海一般的菜場裡,很難買到牛筋,以至於我當年到山西平遙見到牛筋,便喜不自勝,千里迢迢地帶了回來,還捨不得喫,想留到過年;結果沒承想,全臭了。其實,上海還是能買到牛筋的,在大一點的居民聚居區,往往有一個專門售賣清真牛羊肉的地方,是為照顧少數民族及特定宗教的。在那裡,經常可以見到放在一邊的長長的像帶子一樣的白色東西,那便是牛筋。 菜場裡還有一種漲發好的牛筋,往往使用了雙氧水、甲醛以及吊白塊之類的化學物品,而且口感也不好,不建議購買,還是以新鮮牛筋為好。 牛筋是牛腿上的筋,以後蹄的筋為佳。前蹄的筋又細又小、形扁,後蹄的筋,則不一樣,又粗又長,是圓形的。上品牛筋,色純白,無皮無毛,長可達一米,併排三四根,整整齊齊,乃是上品;劣質的牛筋,色灰暗,沾帶血絲,聞之有羶味,不宜購買。 等買好牛筋,奉勸你千萬不要拿回家去自己切,你們家可能沒有那麼快的刀。要切牛筋,還非要用到攤主的那把快刀。牛肉攤上,往往有把小刀,連柄不過一虎口長,寬也不過三指,卻極鋒利,任是牛筋,也是見刀而斷。你可以告訴他要切多少長短,並請他幫你把並在一起的牛筋分開,想那攤主本是解牛庖丁,所謂輕車熟路,一會兒便能弄好。 牛筋洗淨後,放到冷水裡,水以剛蓋沒牛筋為準,開大火併加料酒燒煮。等到水開後倒去,再次洗淨牛筋。另取一大鍋,放入足夠的高湯,將牛筋放入,加料酒以及一兩片薑,待高湯沸騰後改小火燉煮。牛筋本身無味,故要用高湯,若有牛肉湯,則是更好;薑衹要放一點點就可以去腥,多了反而串味。 牛筋燉上之後,要先煮三四個小時,火切忌大,湯則要多,那樣才能煮酥而不會粘底。在燉的時候,可以調弄一下京蔥了。京蔥,除了這牛筋煲,上海人從不食,哪怕肯德基的京蔥卷,在上海也賣得不好。京蔥是一種又粗又長的的蔥,與上海人喜用的小香蔥相去甚遠,一根京蔥便有一斤,是個大家夥。買來後,先剝去外面的老皮,切下蔥綠的部分,留下的蔥桿,外面是蔥白,裡麵包著翠綠的蔥心。切開蔥白,將蔥心取出,再將蔥白切片,蔥心切段。 京蔥這物最奇,生的時候,爽脆可口,一經火燒,便酥爛不可食了。所以,京蔥不要急著下鍋。等牛筋燉了三小時左右,可以開蓋加一點鹽,牛筋不易入味,因此鹽要分幾次一點點地加,把鹽分燉到牛筋裡去。若一次放得太多,牛筋外咸裡淡,就不行了。另外,若是有鹹肉湯的話,可以放入,效果更好。 等放好了鹽,用筷子戳一下,若牛筋已經酥透,就可將京蔥的蔥白放入,並且加入幾滴醬油以著色。再燉上一個小時,便可準備裝盆了。先要將牛筋從湯水裡撩出,用筷子挾去已經煮爛的蔥白。另起一個油鍋,放入蔥綠切成的絲爆炒,再加入牛筋炒勻,放在陶煲裡煮沸,再撒上蔥心,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 若是牛筋夠好,此菜亦可白燒,口味更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配色欠佳,如果用深色容器成盛裝,效果應該可以好點。

閣主的上海話帶著蘇州話味。:)
閣主的上海話帶著蘇州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