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2年8月18日
地點:上海書展上海熱線現場演播室
語言:上海話
主持人:付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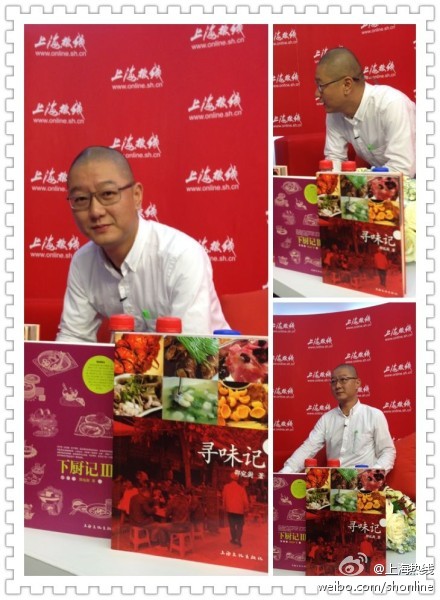
時間:2012年8月18日
地點:上海書展上海熱線現場演播室
語言:上海話
主持人:付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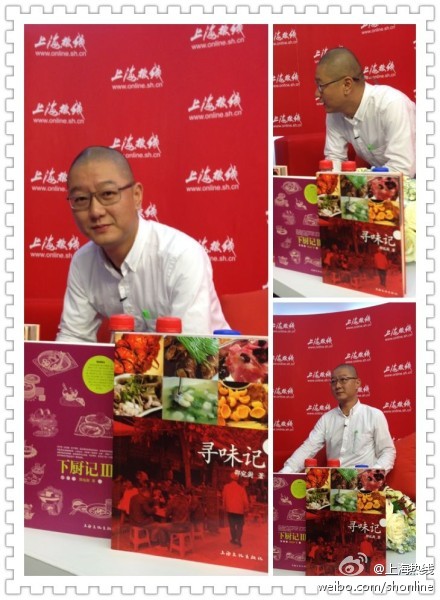
新浪曾經有過一篇標題文章,叫做《紅燒肉的真諦》,據說很轟動,我慕名前去觀瞻,不料那篇竟是我寫的《蘇式紅燒肉》。後來留心查了一下,這篇文章是我所有的菜話中回貼最多,轉載最多,而且也是學的人最多的。《蘇式紅燒肉》中講到好的五花肉,夾精夾肥有許多層,有的人不信,後來親眼見到了才知我所言不虛;我還說這種紅燒肉需要燒兩三個小時,但有許多朋友覺得燉得太爛;又有朋友說糖放得太多,太甜了…… 其實,我說的燒法,衹是大多數蘇州人的燒法,許多朋友本不是蘇州人,當然不能一下子接受別地的口味,不過說來也容易,喜歡肉硬一點的,縮短一點煮燒的時間,不喜歡太甜的,就更容易了,少放些糖嘛。 其實,今天要說的這道菜,也要用到五花肉,肉不是很軟很糯,也不是很甜。當然,五花肉就是肋條,買沒有骨頭的,層數分得多一點的,一斤左右就可以了。買肋條要注意,不要靠近肚子那裡的肉,那裡的肉看上去薄,特別是瘦肉部分,幾乎是薄薄的一層,然而「筋筋襻襻」很多,永遠都燒不酥的。豬肉買來,切成常規紅燒肉的大小,放入冷水中加料酒煮燒。 這道菜,還用到一樣東西,叫做「墨魚」,經常會和幾種「近親」搞錯。章魚就經常和墨魚搞錯,章魚的須是和身體長在一起的,共有八條,所以也叫八爪魚;而墨魚的須要多一些,而且和身體是分開的。墨魚就是烏賊魚,傳說中會噴出墨汁來驅敵的那種怪東西。墨魚也經常和魷魚搞混,區別在於墨魚是白色的,魷魚是紅的,墨魚有一片船形的骨頭,魷魚沒有。 說的墨魚的骨頭,那是種很神奇的玩意,很硬、很脆,卻是奇輕。墨魚骨可以用來擦鐵鍋,擦得非常乾淨,甚至有人訛傳去污粉就是烏賊魚骨磨的粉。因為非常輕,烏賊魚骨還可以用來給小朋友們做玩具,在上面打個小洞,插入一根棒冰棒頭,貼上一張三角形的紙,赫然就是一隻小帆船了,用吹一吹,還真的能夠行駛呢。 以前有人專門走街串巷,收購中藥材,他們嘴裡一直喊著「雞肫皮、甲魚殼」,那時的人們,喫雞的時候,總會小心地剝下雞肫皮,曬乾後等著他們來收購,大的可以賣三分,小的、破的賣二分;甲魚殼其實是甲魚的背,同樣也可以賣錢。他們也收購烏賊魚骨,據說烏賊魚骨磨成的粉有收斂的作用,可以治療潰瘍腫痛等病,民間也常用烏賊魚骨催奶、安胎等。 以前,烏賊魚並不是很上臺面的東西,衹是上海人家的家常小菜,無非就是紅燒而已。寧波人倒是深諳烹製墨魚之道,寧波菜中的「墨魚大熇」,亦算是當家菜之一,「熇」是方言,就像「蔥熇排骨」一樣,「熇」是久燒的意思。墨魚大熇選用大的墨魚,將墨魚掏空後,與肉一起紅燒,最後將墨魚筒切成圈條裝盆,算是很地道的功夫菜了。 衹是,墨魚大熇,雖是好菜,卻極費功夫,燒得不夠,不入味不說,烏賊硬得像橡皮筋,咬也咬不動,燒得時間太長,烏賊酥而無勁,嚼上去就像豆腐乾似的。所以這道菜,等閒之輩不敢問津,大的墨魚很貴,又極易縮,水平不濟的話,花了上百元買原料,做出來一點點東西,又不甚好喫,任何人都會喪失做菜的信心。 不過,卻有一種討好討巧的做法,就是用小墨魚來做。小的墨魚,一斤不到十元,反正本來就小,縮也縮不到哪兒去,更妙的一點,小墨魚嫩且有彈性,比大墨魚更容易調弄。一斤五花肉,最好配上三四斤的小墨魚。 小墨魚買來,從一邊剖開,由於墨魚小,不必象弄大墨魚一樣從裡面掏空而不弄破身體,大墨魚是切成圈喫的,而小墨魚喫起來一口一隻,若不剖開,裡面全是醬汁,喫多了會膩。將小墨魚剖開後,挖出肚子裡有所有東西,棄去,只剩身體和須。注意,烏賊的眼睛在須的頂端,也要挖去。 「墨魚大熇」也叫「剝皮大熇」,關鍵就是要先把墨魚的皮剝去,皮是煮不爛的,留著的話,大大影響口感。小墨魚也要把把剝皮,薄薄的一層,也很容易剝掉。洗剝乾淨後,將小墨魚連同須腕,一起倒入煮著的五花肉中,可以再添一點料酒。 煮多少時候呢?先煮半個小時,然後放一點生抽,三四調羹左右,各種牌子的生抽色澤、味道、鹹度都不一樣,要靈活使用。我以前曾經介紹過李錦記的錦珍生抽,最後發現海天的金標生抽王來得更好,色淡味鮮。 生抽是用來著味的,大約再燒半個小時左右,將五花肉和小墨魚一起倒出在敞口的炒菜鐵鍋裡,用大火開始收乾。收乾的過程中,要加入老抽著色,以前做菜不分生抽、老抽,只用醬油,所以燒出的菜味道夠了,色澤偏黑,如今可以分而使用,不妨少放一點老抽,色澤淡一些,喫起來也輕鬆一點。 又要放糖了,不過這次的墨魚乃是源於寧波,寧波菜偏咸不像蘇州菜尚甜,所以糖可以放得少一點,在江南的紅燒中,加糖不僅僅是為了甜味,同時也是為了用糖的粘度將醬汁粘裹在物料表層。糖最好是冰糖,冰糖不膩,加了糖之後,要注意翻動,否則容易粘鍋,如是直到湯汁收乾,就可以起鍋裝盆了。 這樣的小墨魚大熇,五花肉不是很爛,卻很鮮,小墨魚嫩而有嚼勁,這樣的一大碗,四五個人一頓就可喫完,味道鮮美,又很「下飯」,大家不妨試試。最後補充一句,許多人,將「墨魚」寫成「目魚」,其實目魚是「比目魚」或者「虱目魚」的簡稱,那兩種魚,都是真正的「魚」。
中國人好講究名字,起個菜名,都是弄點意境討個綵頭弄個巧,「金銀蹄」、「如意菜」算是吉祥的的,「貴妃乳」、「西施舌」就有點嚇人了,至於香港人年亱飯上「金玉滿堂」、「富貴盈門」則完全讓人不知所云了,這些菜在不同的店裡,完全是不同的名字。 上海人「崇洋迷外」是出了名的,各位不要駡我,我說的是「崇洋迷外」,並不是「崇洋媚外」。在我看來,此詞並無貶義,衹是個現象罷了;再說了,上海人眼裡衹有歐美算「洋」算「外」,其它地方皆是鄉下。最近的二百年來,但凡醫學文化科學聲色之高者,皆出歐美,一個落後的地方嚮往好的東西,是件好事,固步自封妄自稱大才是要命的。 這不,什麼漢服古風在上海成不了氣候,至於紅歌會憶毛社更是沒有市塲,倒是西域習俗被閙得風生水起,玩玩情人節萬聖節麼也就罷了,我實在搞不懂感恩節和超級碗,上海人起個什麼鬨? 在上海,但凡沾個洋名,就能好賣一成,這也難怪大牛、二妞到了上海就成Jack和Marry了。又如好好的櫻桃不叫,非要喚作車釐子,也挺好,小輩上海人不能準確發音「櫻桃」反倒不雅。 記得有家素菜館,叫做「普羅旺斯」,生意紅火了得,乃是家父有段時間的午飯食堂,衹是和法國菜壓根沾不上邊。 今天要說的東西,也有個洋名,叫做「羅望子」,和「普羅旺斯」聽著差不多吧? 羅望子是什麼?一種熱帶植物,源於非洲,由埃及傳至歐洲及中東,再由絲綢之路到南亞,如今雲南頗多,上海人從不曾見。這種植物外形象是蠶豆,其色褐,其殼硬,民間俗謂「酸角」,此物極酸,空口食之有「倒牙」之感,雲南常用來代替烏梅做酸梅湯;又有一種,長得是一樣的,衹是味甜,即名甜角,雲南的小孩子就當作糖菓來喫。酸角、甜角並不能從外形來分辨,乃是貨主事先分好了賣的,當與其種有關。 此物美國也有,叫做tamarind,據說詞源來自中東,是「印度蜜棗」之意。美國的品種,不分酸甜,沒有酸角那麼酸,也沒有甜角那麼甜,平時當作零時喫很是開胃,用來燒小排也不錯。 Tamarind在亞洲超市和墨西哥超市都有售賣,有時老外的超市也有,袋裝的盒裝的都有,西餐中用處也不少,據說有「嫩肉」奇效。買羅望子,挑大顆而重的買,遠望外殼有光澤的才好。 所謂燒小排,上海人傳統所說的「小排」現在叫做「雜排」,不但在美國,就是在上海也很少見了,我們就改用「肋排」來做,最好是肋排的前段,硬骨短而軟骨長,容易切割。美國的超市有一切橫切的肋排賣,整條寸許寛的肋排,乃是機器切成,這種最好,買上一二條來,在二骨中間切開,即成小塊如骨牌大小。切的時候不要貼著骨切,否則一燒骨會掉出來。 取十來枚羅望子,剝去外殼,裡面的籽是連在一起的,比外殼顏色更深,表面有些黏黏的,不新鮮的就乾了。 先將小排出水,取個鍋把小排放入,用水蓋過,燒至水沸後再稍煮片刻,鍋中血沫一片,關火後將每塊小排仔細洗淨,再把鍋也洗淨,然後重新放水將羅望子和小排同煮。 有白煮和紅煮二種方式,前煮加鹽後者放生抽老抽,我還是比較偏向後者,因為白白的小排,除了在湯中之外,實在令人提不起食慾。 我的做法是把水蓋過小排和羅望子,加生抽老抽和糖,大火燒沸後改成中,時常翻攪以防粘底,半小時後再改大火,再常攪動直至收乾。 此菜全程不用小火,因為肉塊小,所以可以這麼做,如果大的話,還是需要燉一燉的。成品色澤亮紅,與上海的糖醋小排有異曲同工之炒,然而酸味則更和順柔綿,實在是很新奇的味覺體驗。 據說「羅望子」的名字得自於某位羅姓農夫,專種此種植物,家中止有獨子一名,遂給此物取名「羅望子」,乃是「羅家望子成龍」的意思。怎麼樣?一點也洋氣不起來了吧? 有一種說法尚為可取,此物由泰國傳來,乃是「回望暹羅」之意,最早見於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誌 》(1175年 ),反正不是個洋名。亦有人寫論文說酸角並非羅望子,惜傳播不廣,本文仍用民間俗稱。 及此,讓我想起另一個名字的由來,也頗可增笑。說是美國印地安,乃商紂王派出去的人,這些人九死一生分別到了美洲之後,見面時互致「殷地安」,乃是祝福故鄉安康的意思,久而變成了「印地安」。有人還以此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文章旁徵博引來證明美國人乃是中國人的後代,我衹能嘆一聲:有病早治。
有些東西,人們漸漸地習慣了工業產品,比如水餃,上海人本不食水餃,但為了貪圖方便,加之好的品牌,味道也的不錯,水餃越來越受到青睞。然而,有些東西則不一樣,縱是有現成做好的售賣,但總是比不上家庭自制,蛋餃就是其一。 市售的蛋餃,看似顏色均勻,大小相仿,相喫起來既無蛋也無肉,更少了一股蛋餃必不可少的香味;那種蛋餃,個頭雖小,喫口卻是死硬,乃是攤主用羼了水的蛋液,做了大蛋皮,用杯口圧出圓皮子來,包肉製成,完完全全地背離了「蛋餃」的精神。 正宗的上海蛋餃,是在「灶批間」(滬語「廚房」)裡,用鐵勺做出來的。小年夜,昏黃的燈光下,一隻煤餅爐子,風門關得很小,爐口的火只見一點暗紅。一個十歲左右紮著小辮的女孩,穿著有點破的棉襖,做著一隻又一隻的蛋餃。由於天凍,小女孩不停地跺著腳,時不時地還被媒爐的煙熏得咳嗽幾聲……這便是生活,過去的一種頗算幸福的生活,再過兩天,大年初一,小女孩就能穿上新衣服,打扮得像個小公主,拎著奶油蛋糕跟著父母去拜年,興許,可以拿到壓歲錢,可以買幾本心愛的書了。 如今的生活更幸福,衹是小女孩們哪怕過年也要彈琴學英文,再沒有時間做蛋餃了。其實,現在做蛋餃,一來不用受媒爐熏熬,二來買蛋買肉不用憑票,其實大可放鬆精神,在現在的幸福中回憶一下過去的幸福。 蛋餃配料簡單,蛋液、肉糜,分別加鹽、加料酒,拌勻,蛋液中不妨加入幾調羹油,製作方便,蛋皮也更膨鬆。蛋餃的關鍵,在於一塊板油,板油是豬肋下的油膜,受熱會出油。做蛋餃的鐵勺有講究,不用太大但要圓,最好形狀像個半球。 先用火將鐵勺燒熱,放入板油熬一會,第一次熬,要讓鐵勺喫透油,往後,就方便了。等鐵勺燒熱,熬出油後,將板油取出。臽一調羹蛋液,倒入勺內,隨著滋滋的聲響,輕輕地轉動手腕,讓蛋液鋪滿勺底。然後,不用等到蛋液完全凝固,即可挾起一小團肉糜,放在勺子中央,等到邊上的蛋液凝固,用尖筷子小心地挑起一邊的蛋皮,掀起後,蓋上肉糜,同時順勢側翻鐵勺,讓尚末凝固的蛋液流到蛋餃邊上,合攏兩面,凝固即可。 第一隻蛋餃往往會失敗,主要是鐵勺受熱受油尚末均勻的緣故,做上幾隻,就會好的。每做一個蛋餃,用筷子夾著板油擦一遍鐵勺,就不用再放油了。做蛋餃的時候,火千萬不可大,所謂「蠅頭小火」即可,否則易焦,賣相不好。 蛋餃做好,不能就喫,因為肉還沒熟,用大火隔水蒸上二十分鐘後,就算成了。蛋餃往往是放在湯裡喫的,然而饞嘴的小朋友多半已經在大人那裡軟磨更纏喫了許多。蛋餃放在雞湯裡最好喫,若是加入黃芽菜絲,吸去油水,更加味美。

閣主的上海話帶著蘇州話味。:)
閣主的上海話帶著蘇州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