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前幾天的頭條是《單獨活 勞改死》,說的是這幾天大陸熱議的兩件事,分別是「夫妻雙方有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允許生第二胎」以及「廢除勞動教養制度」,至於「活」和「死」,前者的「活」指的是新法律的通過而後者的「死」,指的是舊制度的終止。 活,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狀態,不但誰都希望活著,而中國人,又特別講究喫活禽、活獸、活魚、活蝦、活螃蟹、活甲魚……,反正,只要是動物,中國人最好是看著它們被宰殺,看著被開膛破肚。中國人,大多是底層民眾,除了動物之外,沒人比他們更低了,因此宰殺動物以及觀看宰殺動物,可以過足壓迫欺侮的癮,不至於整天只是被別人壓迫被別人欺侮。 中國人被騙慣了,處處得防著一點,如果不是親眼見到那些東西是活蹦亂跳死在面前的,怎麼保證他們就是正常被宰殺的呢?萬一是病死的呢?萬一是被毒死的呢?所以,還是看著它們被殺,來得比較放心。 據我所知,至少上海人、廣東人、香港人,他們講究活殺的,是因為他們的烹飪理念中認為越是鮮越活的食材,烹調出來的效果越是新鮮,而且這幾地的人,也真有本事喫出哪些是凍過的食材,並且起了個專有的名詞,喚作「冰箱氣」,可見一斑。 前幾天,新聞裡說了一件事,說是上海決定從農曆的正月初一開始到公曆的四月三十日為止,停止銷售活禽,為了預防禽流感云云。新聞中,電視臺採訪了一些民眾,大家在電視中紛紛表示「不喫活禽挺好的」、「統一宰殺讓人放心」、「凍過的不影響口感」等等等等,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反對的聲音,沒人說「我怎麼知道你一定是活禽宰殺冷凍的?」、「你萬一混個死禽進來呢?」,甚至沒有人說「我就是喜歡喫活禽」。 這是怎麼了?諾大的上海,居然大家都舉手讚成「不活」?上海不是沒有禁過活禽,禁了又開放了,當時電視臺去採訪,一眾上海市民都是「喜大普奔」的樣子,可見上海人多麼喜歡活雞活鴨,怎麼現在一轉眼,再次「不讓活」的時候,就沒有哪怕是一個不同的聲音呢? 細想下來,這樣的事情好像很熟悉。但凡是建立新規則新動作,不管內容是什麼,只要是政府「作東」的,電視臺播出的採訪一律是民眾擁護,絕對不會在路人碰到任何一個持反對意見的人,若是過了一段時間,這些規則動作明顯與事實條件相誖被廢除,那麼電視臺採訪時一定大家又會說廢除了會有多好多方便。 這是民眾的問題嗎?恐怕不是,現在的民眾已經很敢說話了,我也做過節目,你去採訪民眾,相對來說,甚至還是牢騷多過讚揚,我絕對不信在場幾十個人,只有同一種聲音。 問題來自哪裡?當然是電視臺,他們不敢或者不願意播出反對的意見,特別是反對政府決定的意見,電視臺「活不過來」。 電視臺「不活」,原因是整個新聞「不活」,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有上萬隻死豬出現在黃浦江時,我們的新聞衹告訴了我們數量,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豬是怎麼死的,這樣的死法是正常還是不正常的,如果是不正常的對我們人類有什麼危害,如果是正常的為什麼往年沒有死豬流到上海來?他們也沒有告訴我們到底有多少死豬不是通過黃浦江流入上海而是通過產供銷渠道流入上海的,反正,他們幾乎什麼都沒說。 有時,「不活」的食品給活人喫下去,是要喫死人的,噢,這不要緊,衹要不當場喫死人,就好了! 衹有新聞活了,人才能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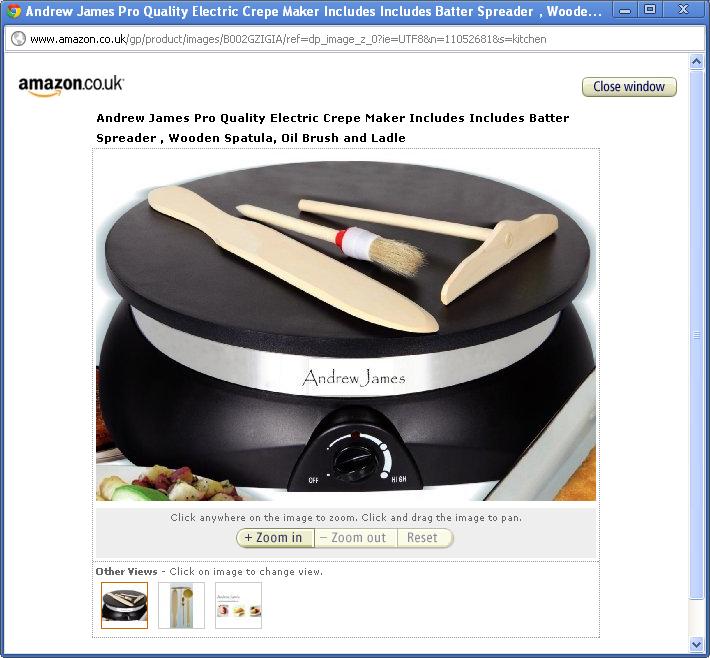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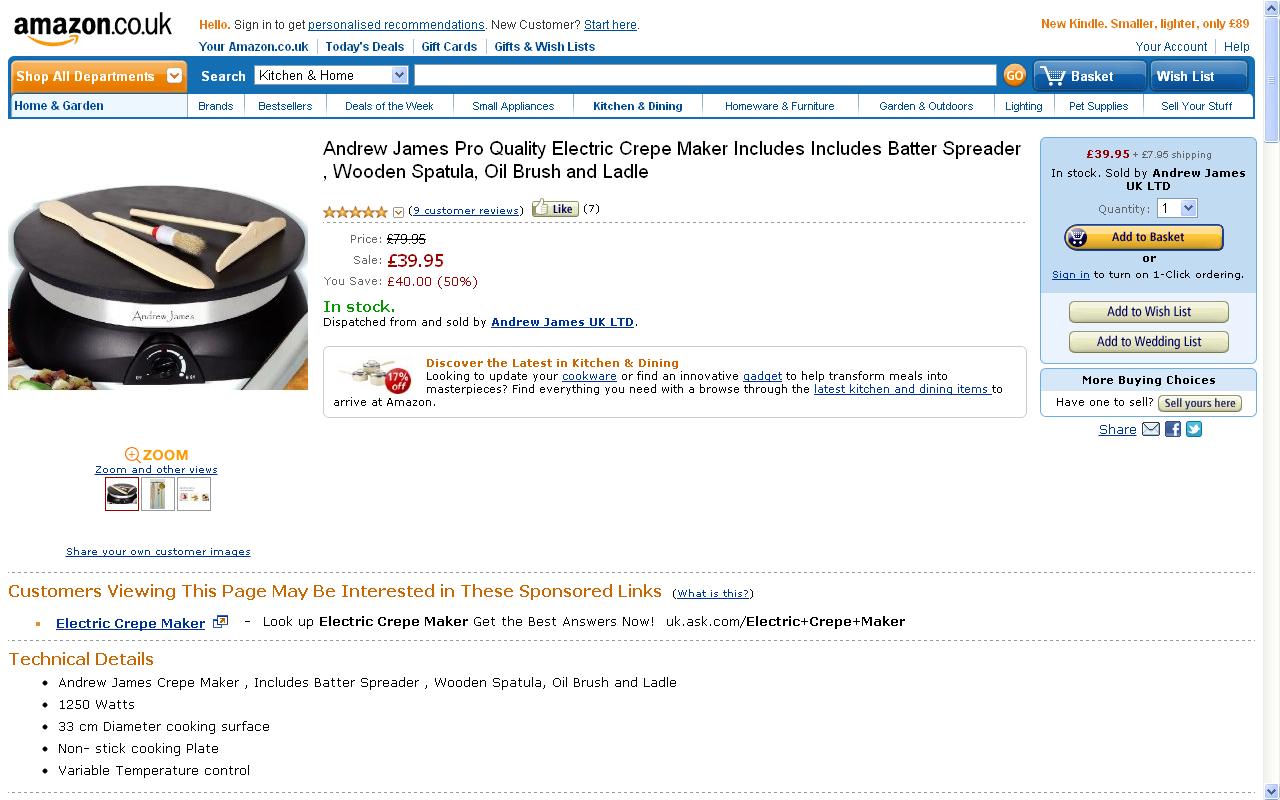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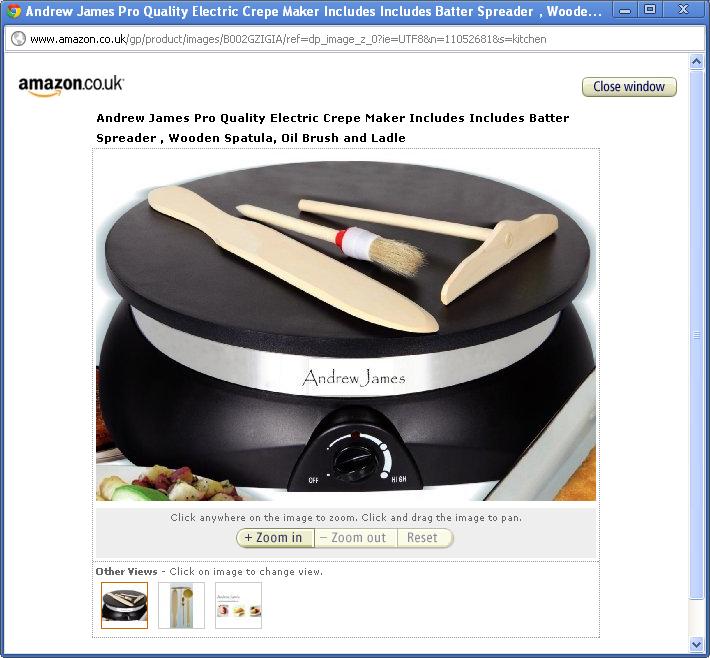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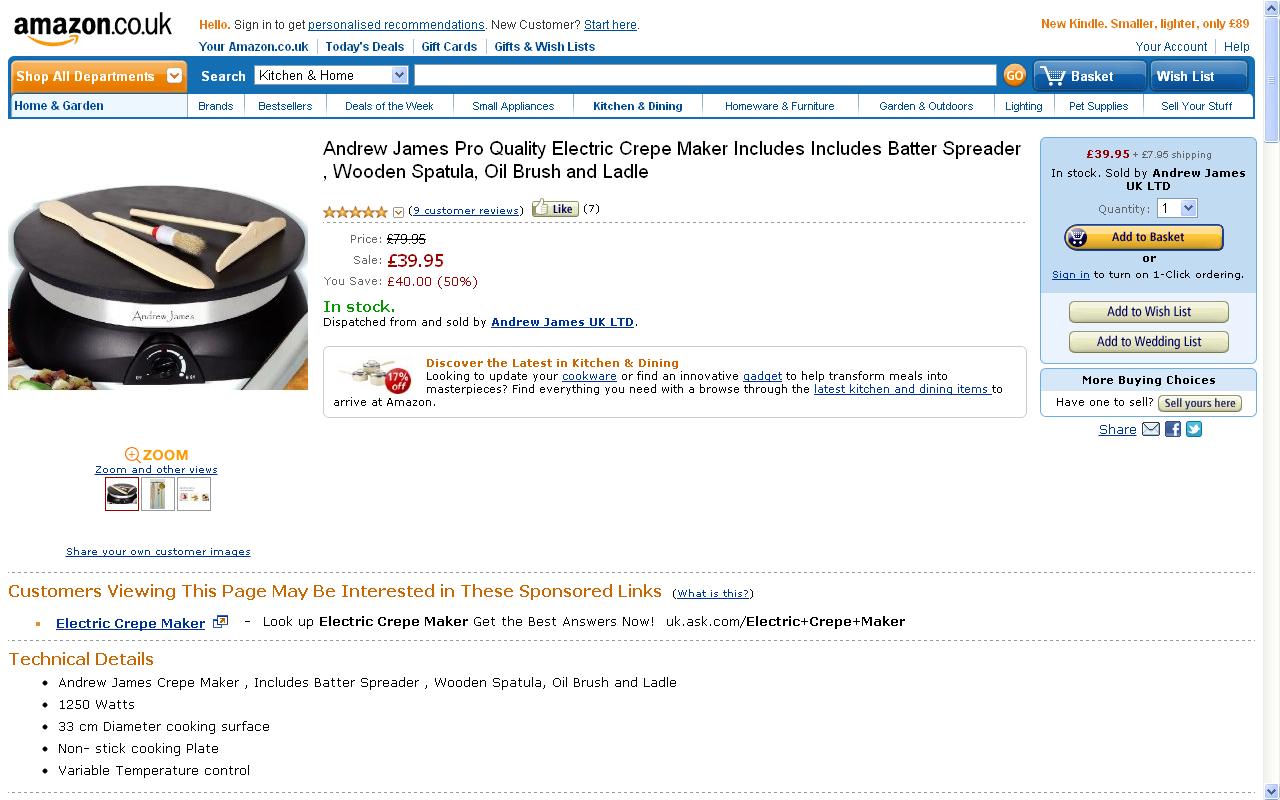
電壓和插座形狀應該不一樣。。。
儂試過用這個做包腳布?老油條哪能解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