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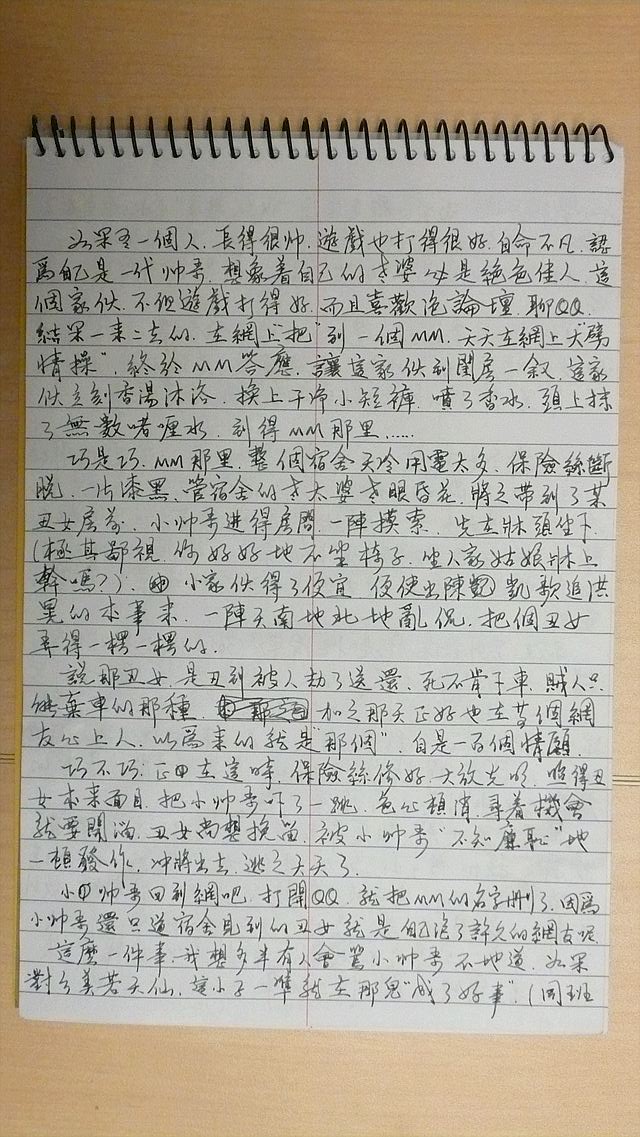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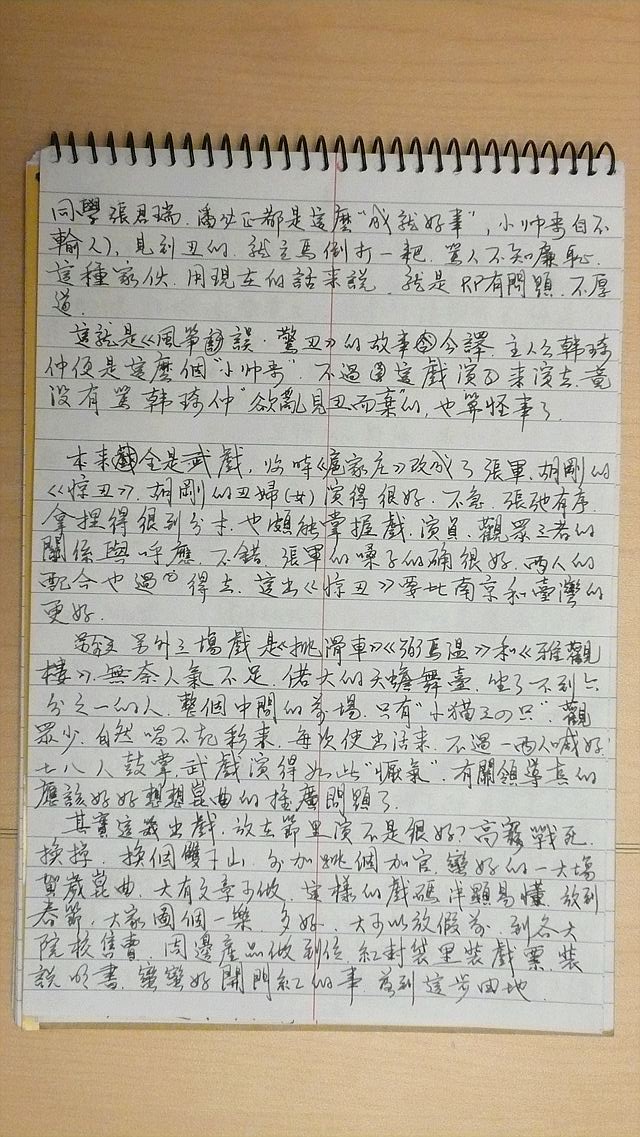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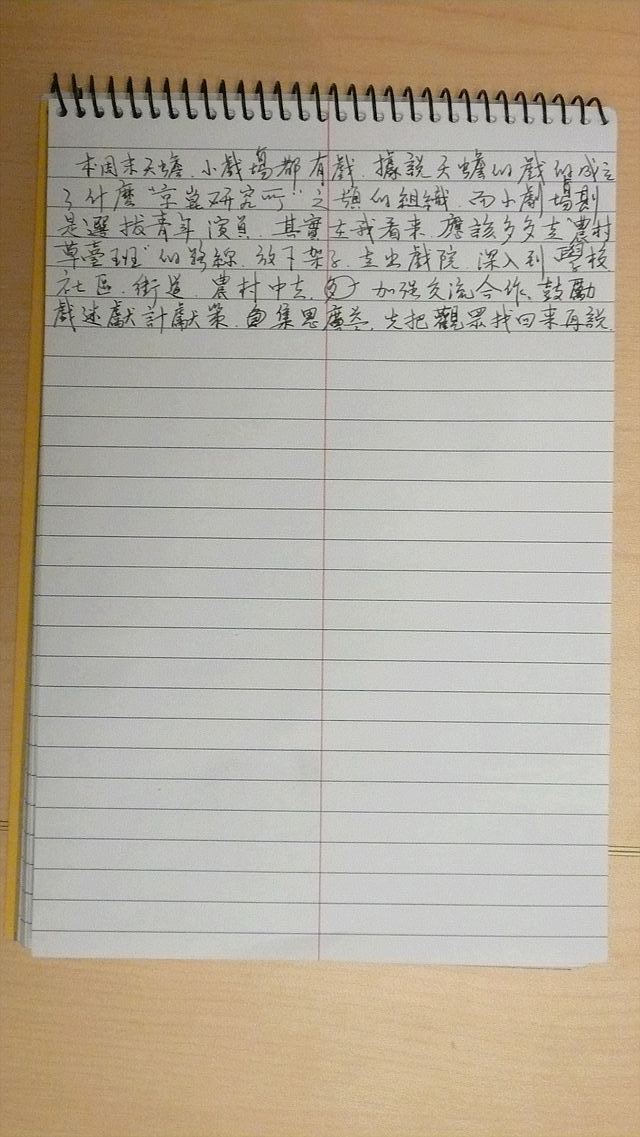

(看看,上昆的行頭,光大靠一台戲就是九套,小點的劇團,哪拿得出這些)

(沒帶大相機,這是用微型相機,在二樓的最後面拍的,效果還可以吧?二樓的最後面,美其名曰「包廂」,其實不過15元一張票,打了折之後)

(大幕尚未合攏,不過就是這麼些人看戲)
關鍵詞:崑曲 崑劇 扈家莊 雅觀樓 挑滑車 高寵 風箏誤 弼馬溫 張軍 胡剛)
Related Posts
牡丹亭賞評 之二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痴迷」成了一個敏感詞彙,變成了一個貶義詞,本來,「痴迷」表現的是一種執著,一種追求,是一個多麼「可愛」的詞啊!就拿崑曲來說吧,愛好崑曲,就要做到「痴迷」兩字,我想,若是拿「痴迷」兩字去用到白先勇、顧鐵華先生身上,他們斷然不會生氣,必定欣欣然而受之。 我也「迷」崑曲,衹是不敢說「痴」,一個人,要有信仰,要有愛好,一旦有東西去「迷」,生活中就會平添出無數的「不亦樂乎」來。得知哪裡有彙演,不亦樂乎?覓得前輩絕唱,不亦樂乎?聽懂了一句雙關,會心而笑,不亦樂乎? 說《牡丹亭》吧,我就「不亦樂乎」地收集了多個版本,其中有CD、磁帶,有VCD、DVD,也有網上下載的MP3,更有我「親臨現場」拍的照片以及縈繞心頭的美妙絕響,怕是一輩子都忘不了的。 牡丹亭,在美國比較有名的幾場中,著名導演Peter Sellars花了一百萬美元在98、99年的時候,搞了一個「觀眾成群往外衝」的「後現代主義」《牡丹亭》,這齣戲,杜麗娘分別由華文漪和黃英兩人出演,這部牡丹亭,我沒有聽過,也沒有見過,找不到任何的影音聲像資料,衹是聽說在《幽媾》一齣中,導演讓杜麗娘在柳夢梅腿上「坐實」,這一「坐實」不要緊,虛的也給「做實」了。只知道黃英擔綱第二幕,那麼腿上的杜麗娘就該是她了,雖然沒有親見,但想像中,柳夢梅腿上坐了個矮胖杜麗娘,張大了嘴高歌,氣勢一定非乏,也一定「鬧」得可以。崑曲這玩意,定要兩人背對著廝磨,方有回味,一旦「坐實」,便無趣味。看來,洋人學中文很容易,但要他們享受那份「閉著眼睛想的獨狠」,就有些強人所難了。 說到黃英的大嘴,天差地別的是張洵澎的「癟嘴」,上海崑劇團於「昆大班五十週年」時,出了一套《中國崑曲音像庫》,該套作品,由周巍峙題詞,程十發題名作畫,實在是收藏佳品。這道「庫」,分別有10張CD和10張DVD,其中的《牡丹亭》一套2張DVD,便是由張洵澎出演的。整部戲,張洵澎都是抿著嘴慢慢哼來,從頭至尾嘴型幾乎不變,亦從未見齒,真真是大家風範,可謂爐火純青也。 那套DVD中與張洵澎配戲的是蔡正仁,上海崑劇團的團長,可能是「油水」太多的緣故吧,蔡團長近年來越發的胖了起來,大腹便便的柳夢梅,不管唱得如何,形象實在不敢恭維,沒有了青春年少的感覺,倒有些惡少調戲良家婦女的意思。 有人說,蔡正仁老了,老了扮相自然不好,這又使我俞振飛來,顧鐵華基金會出了一套VCD,其中有《玉簪記 琴挑》一折,是俞振飛88歲時唱的,雖說一開始臺步稍有踉蹌,可俞振飛實在把潘必正刻畫得好,看了幾分鍾後,便再不覺得是個老人在演,衹是覺得少年書生可愛得緊,調皮得緊。 俞振飛的調皮,早在一九五五年與梅蘭芳演齣電影版遊園驚夢時,就可見一斑了。記得其中有一段,柳夢梅雙手縮在水袖裡,在杜麗娘肩上推了一把、搡了一把,著實天真純情,倒不覺得在看男女歡會,更給人一種「兩小無猜」的可愛勁,真真發喙。這個版本的牡丹亭,最好配合梅蘭在一九六一年為中國戲曲學院戲曲表演藝術研究班的報告一起來看,那份告,梅蘭芳對遊園驚夢逐句講解,將表情、身段、部位、手勢做了詳細的分析,將此報告熟讀,再對照著看大師們的表演,方可知道什麼叫做「恰到好處」,知道什麼叫做「心靈的交流」。 梅蘭芳電影版裡,可以看到梅蘭芳的臺步,欣賞「飄著走」、「人移裙不動」的絕活。戲中,言慧珠飾演春香,活潑可愛,衹是言慧珠著實美麗漂亮,真真是演正旦而不是貼旦的料,那扮相竟比「死魚眼、水桶腰」的小姐好看許多。可是與梅蘭芳配戲,言慧珠就算再可愛,也衹能演丫環了。言慧珠實在是個可愛的人,記得小時候的語文老師說過「可愛」的意思就是「可以去愛,值得去愛」,言慧珠最「可愛」也是最「可悲」的是1966年的9月11日,她化好了妝,穿了戲裝,在胸前掛了一塊「我要唱戲」的牌子,於浴室自縊了。俞振飛痛失愛妻,慧哉!戲壇裡頓殞巨星,嘆兮! 與其說言三小姐是自殺的,倒不如說她是被那個只識花鼓戲的反革命家屬害死的。雖然那時含恨自殺的還有嚴鳳英、上官雲珠、小白玉霜等許多著名演員,然而,言三小姐的死,是她們中最華麗的,最令人扼腕的…… 說到花鼓戲,不得不說陳士爭了。陳士爭是一個湖南花鼓戲的演員,不知怎麼去了美國,又不知怎麼搭上了美國林肯中心,於是搞了一個「鴨子充鴛鴦」的全本《牡丹亭》,這場戲上演於1999年,共六場四天五十五折,戲臺、音樂比尊古制,基本上一桌兩椅而已,音樂也不像其它的好多版本用了西洋樂器,而是純用笛子領綱,配用中國絲竹。然而陳士爭忘不了他的花鼓戲,不但在過場中用了許多「花鼓歌」的調子,甚至把湖南話也搬上了崑曲舞臺,真是服了他了。這個版本最不了的是「春香」,實在是醜得可以,這都源於陳士爭「就地取材」,不但春香難看,他還用了許多其它地方劇種的演員,使得整部戲參差不齊,有點大雜燴的味道,倒蠻符合「美國精神」的。 好在男婦主角科班出身,分別是北昆的溫宇航與上昆的錢熠,錢熠雖說不是「當家花旦」,但總算是「喫過蘿蔔乾飯」的,演與唱,都還可以。衹是橫看豎看,只覺得好好的男女主角,偏偏給導演弄壞了。首先是服裝的設計,本來,杜麗娘的立領緊扣、水袖飄逸,很是美麗;結果在陳士爭版裡,杜麗娘穿了一件「繡了黃龍的鳳袍」,寬袍大繡,不倫不類之極。立領變成了無領,當然也沒什麼鈕子可扣了,肉露得一多,反而不變了,至於《山桃紅》中的「和你把領扣兒松」卻再怎生個「松」法。領口露點肉倒也罷了,怎奈也是《山桃紅》中柳夢梅居然把杜麗娘的衣服給「剝」了下來,而且繫帶還是杜麗娘自己給解開後,讓柳夢梅牽著衣袖才脫下的,看那杜麗娘心急如此,完全少了「半推半就」的意境,倒有些女朋友怕男朋友手笨,先把胸罩帶子解開的「體貼」,一開始便急成這樣,不知「俺可也慢掂掂做意兒周旋」,要待如何,衹能一笑了。那架勢,使我想到歐美電影來,男女主角進得房裡,女主角不等門關上,便脫起衣服來…… 陳士爭版還有一個缺點,就是錢熠唱得太咬牙切齒了,加之錢熠眼睛又大,眼白多眼黑少,待唱到《尋夢》《豆葉黃》「忑一片撒花心的紅影兒吊將來半天」時,雙手平舉,兩眼黠出,不似在演《牡丹亭》,倒活脫脫是一出閻婆惜的「活捉」了。 陳士爭版共十八個小時,保羅出的DVD衹有兩張,還夾了兩段評彈,《遊園驚夢》中居然沒有《梳妝》,想必是選輯DVD的人不懂戲的緣故吧。
牡丹亭賞評 之一
清朝的方飛鴻編過一本書,叫做《廣談助》,有點象如今的《演講與口才》,是用來增加談資的,其中第三卷《諧謔》有個笑話,是這樣的:「少年聚飲,歌妓侑酒,唯首席一長者閉目叉手,危坐不顧。酒畢,歌妓重索賞錢,長者拂於衣而起,曰:『我未曾看汝。』歌妓以手扳之曰:『看的何妨,閉目想的獨狠。』」這個笑話,說得實在是好,好就好在「閉目想的獨狠」。 以前有樣東西,所謂「黃帶」,其實就是婬穢錄帶,現在叫做A片或是毛片,那些就是「看的」,而崑曲則「閉目想的」,想的比看「獨狠」,狠在哪裡?聽我慢慢道來。 崑曲,常被稱作「婬詞艷曲」,也有人說不是,說不是的代表人物是袁四爺,哥哥版《霸王別姬》中袁四爺在法庭上,面對檢察官對程蝶衣的指控,從容站起,開言道:「方才檢察官所說之婬詞艷曲」——全場一片寂靜,袁四爺突然用力猛拍欄杆——「實為大謬」,全場竟鴉雀無聲,四爺又說:「當晚程所唱者,牡丹亭遊園一折,眾所周知,乃國學文化中之最精粹。何以在檢察官口中,竟成了婬詞艷曲了呢?如此污衊國劇精粹,不知是誰專門辱我民族尊嚴,滅我民族精神?」這時,場內才有了聲音,是鼓掌聲。四爺慢慢道來,抑揚頓挫,很是生動,也使形象不佳的四爺霎時可愛了起來。 四爺說到的《牡丹亭》,在我眼裡可謂著著實實的「婬詞艷曲」,我這可不是「污衊精粹」,實在是「咱愛煞你哩!」牡丹亭的婬,乃是天下至美至純的婬,牡丹亭之艷,乃是人間極華極美之艷;如此的「婬詞艷曲」,當然是國粹,粹就粹在「婬艷」之上。牡丹亭說的是一個叫杜麗娘的女孩子,在春天遊園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夢中與一男孩子柳夢梅「雲雨」了一回,結果鬱鬱成病,一命嗚呼;再後來,杜麗娘化魂與柳夢梅又「好」了一回,最後柳夢梅開墳掘屍,杜麗娘復活,有情人終成眷屬,皆大歡喜的故事。過去,經常在介紹這部戲的時候,加上什麼「反封建」、「反壓迫」之類的話,把個好好的「婬詞艷曲」弄得不倫不類。 杜麗娘做了一個「雲雨」的夢,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是「發了個春夢」,可每次我說到「遊園驚夢」的時候,總是想起蘇州話中極不堪的一個詞「鬼戳屄」來。鬼戳屄,悄然無聲,蘇州人用來形容某人做事鬼鬼祟祟,有時也用來指「小家敗氣」;可杜麗娘恰恰是被這鬼鬼祟祟弄得一病不起,命赴黃泉。 好了好了,我們先來說戲本,市面上最普通的,要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4月第一版的徐朔方、楊笑梅校註本,作為《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之一,與四大名著等均為同一時期,同一體例下的產品,校勘相當嚴謹,多是從各個本子比對而來;這套叢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註釋詳盡,比如《紅樓夢》的注,會引用「脂本」中的說法,或對比、或類比,光看註解也是一種享受。然而,唯獨《牡丹亭》,注得卻是語焉不詳,頗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恐怕在當年,有些東西還是衹能「意會」——「閉目想」的緣故吧。至於該套的中的《西廂記》,不推薦去讀,讀《西廂》,當然要讀金聖歎批的本子,這是題外話了。還有一種戲本,就是演出本,因為用「上尺工凡六五乙」代表七音,所以也叫「工尺譜」,1924年商務書局出的石印本《集成曲譜》就是這種,這套譜由王季烈、劉富梁編訂,不但嚴謹,而且糾正了許多音律上的錯誤。 戲本介紹完了,我們就一起來讀這著名的「遊園驚夢」吧,「遊園驚夢」是戲的俗稱,其實是戲中的第十齣《驚夢》。這個「齣」字,常被訛為或「簡化」為「出」字,其實意思是有不同的,有時,真不知道簡體字有什麼好。我常開玩笑說,簡體字的目的是要把「黨」改成「黨」,黨當然是要兄弟般的,不能與黑社會沾邊,公有化了,也不存在結黨營私了。當然,簡體字其實在國民黨手裡就打算搞過,衹是沒有成功罷了。 說到國民黨,這幾天連戰訪問中共,著實熱鬧了一回,我想到的不是國共合作,而是台北的那些崑曲檔期。不是有句名言麼,叫做「崑曲的演員在大陸,崑曲的觀眾在台灣」,的確,青春版《牡丹亭》、華文漪與蔡正仁五十一載再攜手《長生殿》等著名的段子,都是在台灣首演甚至只在台灣演。尋根尋根,根在園內,花在牆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