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2年8月18日
地點:上海書展上海熱線現場演播室
語言:上海話
主持人:付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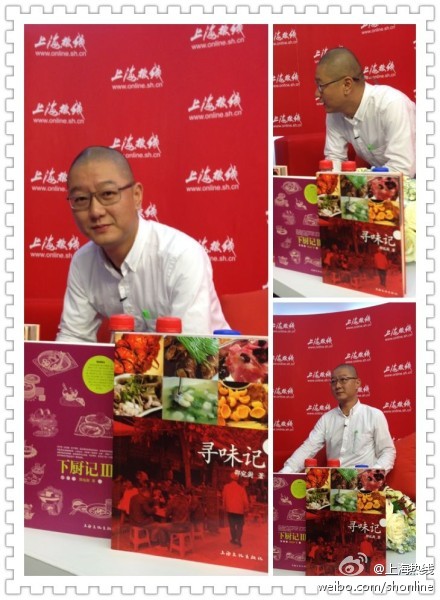
時間:2012年8月18日
地點:上海書展上海熱線現場演播室
語言:上海話
主持人:付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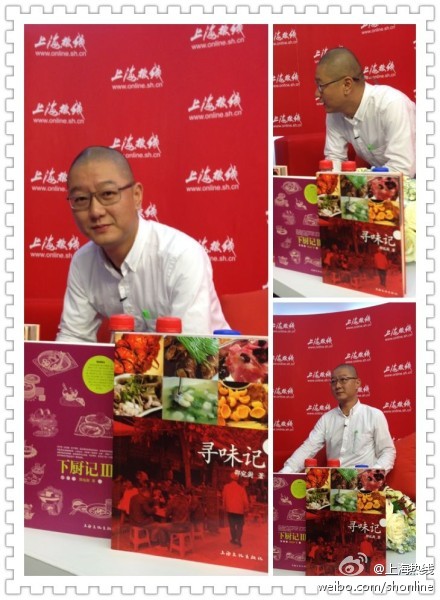
我現在正坐在一家圖書館中,用我的laptop,一臺二手的Thinkpad T430,比新的15吋觸摸屏還貴。雖然是臺有點年份的電腦,但性能相當好,有些配置甚至比新機都高,所以我後來退了「黑五」搶來的15吋觸屏lenovo,買了這臺二手的,裝了個linux操作系統,跑得飛快。最近更是換了個500G的固態硬盤,流暢無比,關於這個硬盤還有個故事,以後有機會再說。 我是怎麼會在圖書館的呢?二天前我不是去了4S店在那兒寫東西麼?那天后來「一事無成」,缺個配件,讓我今天再來。修車說是要二三個小時,4S店後面便是個公共圖書館,我是「蹭網」的。這臺電腦什麼都好,就是太硬,背著走了一大段路,挺累的,美國的「後面」有時一二個英里都有可能,下回應該帶著蘋菓電腦出來。 說回家宴,阿杜買糟滷去了,現在就剩我們三個人了。 咦?不是二個人嗎?一個我,一個阿杜,還有個E,阿杜走了,不是應該二個人嗎? 因為又來了個P,P女士。 是這樣的,三個月前,我就和阿杜與E說好了這頓飯,說好請他們二個來幫忙,做我的「下手」;而P呢,我沒有請她來幫忙,衹是請她來「玩玩」。 P是上海某家著名生煎店出來的,到了洛杉磯後售賣上海大小餛飩,研發了各種餡料,在華人圈特別是上海人圈中頗有名氣。因為我當天也有餛飩,存著「露一手」的想法,請她來「玩玩」。結果沒想到,P是個相當有「眼色」的人,裡裡外外從頭幫忙到底,而餛飩更是她一手操辦,我衹是把配料告訴了她,剩下的都是她來完成的。有趣的是,我們交流了一下餛飩的包法,她居然認為我的包得好看;更有趣的是,我一直以為那家生煎店是不用皮凍的,她告訴我是用的。 對了,文章寫到了第四篇,還沒有公佈菜單呢,一直說十道冷菜十道熱菜,但至今還沒說有哪些菜呢!好吧,這就來: 冷菜 四喜烤麩 糖醋小排 上海醬鴨 糟拼 銀芽雞絲 翡翠雞汁蟬衣包 老醋蟄頭 曝醃烏青 荷蘭豆拌牛百頁 醉棗 熱菜 響油鱔糊 閣主拿手腰片 紅燒肉(配白米飯) 汆燙蝦仁 炒時蔬 臘味合蒸 火腿煎鮮貝 芙蓉黃魚捲 金湯醋椒魚…
我年輕時曾經很崇拜一個人,名字我就不說了,否則真要成個「噴子」了,見一個駡一個。我並不想駡她,我衹是想說別迷信任何的權威和專家,包括我,如果有一天我也能算的話。 這位出了很多的書,是我接觸到的最早專門著眼於美食的古代風俗研究著作,有人說我見識短淺,鄧雲鄉早就寫過《紅樓風俗譚》了,但這位是最早著眼於展示唐朝人喫什麼宋朝人喫什麼的,紅樓的時代,在眼裡都不能算古代。 我那時年輕,她的書出一本我就買一本,一開始,我就想,怎麼有這麼學識淵博之人,可是讀著讀著,就發現猜想的成分很多,主觀臆斷的成分也很多,我就漸漸地不看她的書了。 再後來,我系統地找了古代談風俗飲食的書來看,其實總共也就那麼幾本,都是當時的筆記小說,像是《開元天寶遺事》、《酉陽雜俎》、《世說新語》、《太平廣記》、《武林舊事》、《夢梁錄》、《東京夢華錄》、《揚州畫舫錄》以及《清稗類鈔》等,那些說唐風宋俗乃至明清生活的基礎書,就在這幾本中來來回回地抄。 有些書,要自己去看,否則被騙被賣了,都不知道,就拿文首那位來說吧,她寫過這麼一段:「在唐代,在品嚐櫻桃的種種方法中,最普遍、最受歡迎的吃法,始終是乳酪澆櫻桃。五代人王定保在其所著的《唐摭言》中記載有這樣一則軼事,在公元878年的一次新進士宴上,主賓們一共吃掉了幾十棵樹產出的櫻桃,僅用以澆佐櫻桃的乳酪,就用去了不止好幾斗。」 我以前每每讀到這一段,就很羨慕唐朝人,用乳酪澆在櫻桃上喫,唐朝人就懂如此享受,真是讚啊! 後來,我讀到了原文「唐摭言‧卷三‧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日以銀一鋌資覃醵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碩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盎,亦不啻數升。」 不看原文不知道,看了才發現我以前是有多淺薄。首先,乾符四年,是877年,而不是878年;其次,那位女士說主賓們喫掉了幾十「棵」樹的櫻桃,而其實他們是喫掉了幾十「碩」的櫻桃,她並不知道「碩」是「石」的通假字,唐朝的一石(小石)相當於現在的五十多斤;還有,她說澆在櫻桃上的乳酪,用了好幾「斗」,而原文中是「升」,要知道,在唐朝,一斗合十升,這個數字一下被她放大了十倍,唐朝的一升,相當於現在的四兩。 幾百上千斤櫻桃,澆了幾斤的乳酪,算是「最普遍、最受歡迎的吃法(原文)」?這也太小看唐朝人了吧? 真相是如何的呢?要知道,進士喫櫻桃,是當時最熱閙的曲江宴,進士發榜在上巳節前,而狂歡,則在上巳節,不僅是中榜進士歡,乃是舉國舉城歡慶,因為那是個「小長假」。 上巳節什麼時候?上巳節又名「三月三」,相當於現在的清明左右,那時的櫻桃還沒熟透,原文中有「雖貴達未適口」,就是說雖說賣得貴但不好喫,這就像現在秋末就喫到春筍一樣,哪怕賣得貴,但還是不好喫。櫻桃沒熟透應該是酸的,甚至還有點澀,那怎麼辦?加糖唄,但糖是固體的,不容易粘裹在櫻桃上,做成糖漿要加熱,而現成的甜乳酪,是最好的選擇了。至於為什麼那麼多的櫻桃衹用了「數升」糖酪呢?那是那位女士誤讀了,她沒有理解當中的那句「人享蠻畫一小盎」,於是乾脆忽略掉了,原文的意思是「每個人」都用了數升糖酪。 現在問題又來了,一升四兩,數升豈不是一二斤?再加上櫻桃,難不成一人一頓要喫個三四斤甜品?這裡有幾個可能,最可能也最不可能的是唐人胃口比現在人大,從農業的文獻應該可以考證出結果,但我猜可能並不是。第二種可能,辦過大型宴席的人都知道,下面報上來的食物用度的量,如果除以參加的人數,十有八九是會把人撐死的;我朋友公司就發生過一頓年夜飯人均七瓶紅酒一條半煙的故事,當然,這也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時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止增一笑罷了。 從各類的資料來看,唐朝的「酥酪」是一種類似於今天酸奶的東西,而「糖酪」就是加了糖的。我不知道最早誰把「yogurt」譯成「酸奶」的,而我在西寧大清真寺門口喫到的土酸奶也的確酸得要死;從小喫到大的玻璃瓶光明酸奶,也一直是酸酸甜甜的,以至於我從來沒有思考過「yogurt」到底應不應該是「酸」的。 到了美國之後,我也喫酸奶,喫來喫去,有一天突然發現一個問題,美國的酸奶是不酸的,怪不得「yogurt」也被譯成「優格」「優酪乳」呢,不酸的奶製品,不能叫「酸奶」吧? 這篇文章說的是不要迷信專家和權威,有時甚至連自己的口味和口感都不能迷信,不但酸奶如此,連提子也是如此。 我很喜歡喫葡萄,在有一年去了山西喫到了清虛葡萄之後,我就成了葡萄的愛好者了。我丈母娘知道我喜歡喫葡萄,於是我每回去,她都會買好了給我喫。問題是她每回買的都是我們稱之為「提子」的那種東西,雖然二種東西都叫「grape」,但我始終不肯認同提子就是葡萄,因為提子太難喫了。皮厚不說,卻剝不下來,還有點澀,菓肉不甜,還要吐籽;我每回都說我要喫葡萄不要喫提子,但下回去,丈母娘還是買了提子說「知道你喜歡喫葡萄特地買的」,可買了總得喫吧,越喫越以為我喜歡喫就越買,就這麼惡性循環著,以至於我恨死了提子。 到了美國,提子幾乎是一年四季都有賣的,我卻從來看也不看,依然想念我心中的「葡萄」,有次還在韓國超市買到,讓我過了一回癮。後來,偶然的機會喫了一顆青提,沒想到出奇的好喫,皮是脆的,也不澀,也就不用剝皮了,果肉香甜,還沒有籽,真正應了那句「那是你沒喫到好的」。打那以後,我就又愛上了提子,不管是紅的還是綠的,衹要挑準了「seedless」買,都很好喫。 不過美國的提子太甜了,甜到我不再懷疑葡萄汁是加了糖的,美國的葡萄汁甜到不加冰喝不下去,而這提子本身,也是冰箱裡拿出來馬上喫好喫,要是放到常溫,甜得發膩,就不想喫了。 於是,我受唐朝「酥酪櫻桃」的啟發,用不甜的希臘酸奶配對半切開的青提,不出意料的好喫,後來我還加入了藍莓,更好喫;再後來,加入了小核桃肉,那叫一個香啊;再再後來,我把樂嘉杏仁糖壓碎了撒在其中,簡直是放緃的享受。 這篇就不說怎麼做的了吧,這實在是太簡單了,你可以用任何的酸奶配任何的水菓,哪怕配黃瓜番茄都成。我比較喜歡用一個Chobani牌的希臘酸奶,除了菌種外,就是百分之百的牛奶了,既不甜也不酸,「我想」這可能是最接近於唐朝酥酪的東西,衹是「我想」哦! 有許多酸奶中有明膠、果膠、乳清蛋白粉乃至食用香精、奶精之類的東西,我並不是說那些東西不好,它們的確有可能比純的酸奶更香更可口,衹是我不喜歡,好在不管中國美國,成份表中都有標明,大家自行選擇就是了。 最後,什麼都不要迷信,中國也有不酸的酸奶,美國也有酸的酸奶,另外大家如果對古代感興趣,看了一段時間的入門書之後,最好直接找古文來讀,古文和外語差不多,多讀總會有進步的。
松茸鮮肉餛飩,這根本就是個異類。 上海人在聊餛飩的時候,我們說的是「上海大餛飩」,什麼廣東的雲吞、沙縣的名點,都不在討論範圍。 我有個版本的大餛飩,很多人喫了都說好喫,那是我私房菜的存底,豬肉、河蝦仁、乾貝、扁尖、榨菜、開洋。 但我平時一般不做這個版本的,麻類,到了美國之後,小蝦仁倒是也有,不過是海蝦,沒有河蝦那麼鮮。 我最常做的版本是肉和榨菜,或肉、榨菜、扁尖,前段時間發明了豆苗肉餛飩,那樣在摘豆苗時就不會不捨得了,儘管摘嫩的炒來喫,老的可以包在餛飩裡。 豆苗做餡,要先用開水燙過,一大把豆苗,燙過以後衹有一點點。 夢花街的餛飩店參加了「夢想改造家」項目,他們家的餛飩無非就是個頭大,味道極其一般。上海有那麼三家店,舒蔡記的生煎、萬壽齋的小籠、夢花街的餛飩,都是加不了分子拚命減分母的,價格一下來,性價比就飆升。 夢花街上,其實在那家著名的餛飩店朝西,有家安徽人夫妻老婆店,他們家的小餛飩和隔壁的鍋貼都相當好,非要去網紅店的,真是洋盤。 不知道有沒有人回訪夢想改造家的後續情況,我敢說,百分之九十九被改造家庭,依然會過上以前的日子,甚至更逼仄,夢想改造家們的「奇技婬巧」其實也是要佔去空間的,然而並不是面積和佈局讓他們過得不好,是理念,理念很難改造。 我娘說「包餛飩太累了,再也不自己包餛飩了」,我說「我是偷懶才包餛飩,包餛飩多容易啊?!」 我娘說「我不要喫肉餛飩,實別別一隻隻,象喫肉圓一樣,有啥意思啦?」,我說「我就歡喜喫肉呃,阿拉搿搭又沒新鮮薺菜賣。」 我娘說「我歡喜喫菜呃,菜要多!」 但凡有人跟你說「正宗的上海餛飩,皮不是方的,是梯形的」,千萬別信,那就是他買到了沒切好的皮子,然後又被賣皮子的騙了。 上海人最喜歡喫的是薺菜肉餛飩,最好是薺菜加青菜,都是開水燙過才行,衹用薺菜的話,薺菜太乾,但不能加水,而是要餡中加油,一斤餡要加個一二兩麻油,問題是加了油的餡,很難包。 我喜歡包餡大的餛飩,我和女兒都有這本事,可以包出比別人餡大一倍的來。好友洪淵到我家來玩,幫著包餛飩,其餡甚小,我對她說「這是給自己喫的啦,不是賣的!」 刀魚餛飩就是智商稅,我排過一系列算式,按成本來算,58元一碗的餛飩,每個餛飩能攤到0.5克刀魚,照一個餛飩十二到十五克餡來算,單碗刀魚餛飩的成本價在千元以上。 所以千萬別以為自己花八百元喫了碗刀魚餛飩就是大款就是識貨朋友,恰恰相反,洋得沒法再洋的洋盤了。 松茸餛飩亦是如此,浪費好食材罷了,且松茸有股奇怪的泥土味,與餛飩並不是很搭。 韭菜餛飩是上海人不能想像的東西,但是好像與刀魚放在一起就名正言順高大上了。勿要再洋盤了,過去韭菜和刀魚,都是不上檯面的東西,什麼?要吵?我才不和你吵這個,你先搞清楚了什麼叫「檯面」再來,不是貴的就一定上檯面的,你花再多的錢娶個從良的回來,依然……為防女權找茬,大家自己想。 很方地方有用剩菜做包子的習慣,也有的地方包包子喜歡放粉絲、豆腐等,餛飩沒有這種喫法,上海人的餛飩相對簡單,純肉、菜肉、蝦肉,菜肉分薺菜肉和青菜肉,蝦肉一定是河蝦仁,沒有用海蝦仁包餛飩的。 其它餡的,一般都不是家裡包的,比如鹹蛋黃的,好像是每隻餛飩中放半隻鹹蛋黃,想想也嚇人,一碗餛飩有五隻鹹蛋?所以這種餛飩最好喫「全家福」的,吉祥餛飩就有全家福的,吉祥餛飩難喫死了。 耳光餛飩可以論隻賣,是個不錯的謔頭,耳光餛飩的味道袛算中上,主要還是好玩,可以點四隻餛飩加份辣肉,關鍵那時已經十一點鐘了,酒早喝過一場了,這時給碗方便麵也好喫的。(耳光餛飩是上海的夜宵餛飩攤,印象中白天是不開的) 山海關路的餛飩攤也以論隻賣,我有時要二葷二素四隻大餛飩加十隻小餛飩,我在那邊動拆遷的最後幾天把餛飩攤要拆掉的消息發到了微博,據說那幾天去喫的人全都認識我。 據說最後那個老闆拿了十二套房子。 據說後來那個餛飩攤開到了黃河路定興路的華茂飯店,就是我的紀錄片《我愛「四大金剛」》中小豆子出場的那個早餐點。 煎餛飩、油汆(炸)餛飩、生煎餛飩,是三種不一樣的東西,加上冷餛飩,是四種不一樣的東西。 餛飩要好喫,首先肉要經過攪打,放鹽後攪打起勁,我現在用Kitchen Aid的電動手持攪打器,很方便,因為我包一次餛飩就三十八隻,為什麼是這麼個奇怪數字?因為一包餛飩皮一磅三十八張,配一磅肉正好。 如果要一下子包一二百隻餛飩,要用檯式的Kitchen Aid來打肉,如果要再多的話,去找商業用機工業用機,它可能長得比Kitchen…

閣主的上海話帶著蘇州話味。:)
閣主的上海話帶著蘇州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