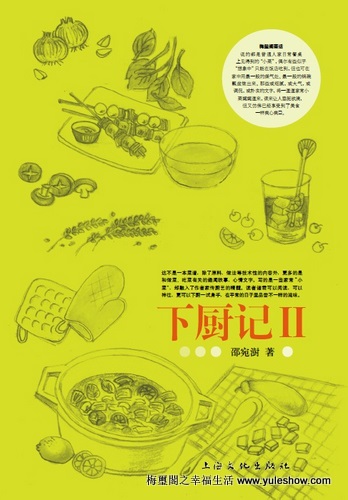
茲定於《下廚記 II》於2011年上海書展首發,簽售會定於8月21日中午11:15,會後將有AA制午餐會,想參會的朋友請私信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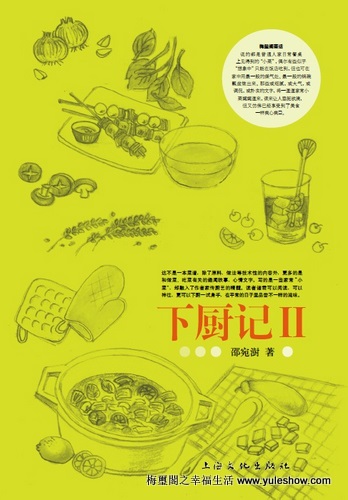
茲定於《下廚記 II》於2011年上海書展首發,簽售會定於8月21日中午11:15,會後將有AA制午餐會,想參會的朋友請私信報名。
上海乃是魚米之鄉,上有蘇錫,下有杭余,秉日月之精華,承天地之靈氣,不但物產豐饒,更有佳餚美饌,實在是個好地方。 上海近湖沿河靠海,多有魚獲,上海人的餐桌上,常有各式各樣的魚,叉扁魚、肉塌魚、帶魚、青鯰魚是海魚,河鯽魚、扁魚、黑魚、白水魚則是河魚,上海話中”河”、”湖”不分,只要是淡水魚,一律稱之為”河魚”。 河魚中有一種叫做”青魚”,體型最大,是上海人極其喜歡的一種魚,由於青魚大,所以並沒有”清蒸全魚”或者”紅燒全魚”的做法,而多是取相應的部位,做成各式菜餚。 青魚頭雖然沒有鰱魚頭那麼大、那麼肥美,不過依然可以做成”拆燴魚頭”和”魚頭湯”,更厲害的,單取魚唇,”煨魚唇”可是一道名菜呢! 魚身,可以剔骨切成魚片,清炒、糟溜都可以,上海的名菜”紅燒肚檔”則是只用青魚的肚皮肉製成,肥美無骨,是一道極享盛名的好菜。若是將魚身連骨切塊,則可以做成蘇式熏魚,雖說蘇式,但也是上海的常見菜式,甚至於”老大房”加以改進後,變成了頗具特色的上海熟菜。 青魚的尾巴,可以做成”紅燒划水”,該菜擺成扇形上桌,煞是好看。青魚身上最值錢的,居然是魚泡泡,一道”煨魚肚”是極”上檯面”、”扎台型”、”吃價鈿”的,難怪有許多飯店用油汆肉皮冒充,以騙”洋盤”。 如今菜場中的”青魚”可謂”只聞其聲、不見其影”,早已見不到”青魚”的身影了,不過”青魚”兩字卻時常可以聽到。君不信?你看菜場每一個攤主都會指著大盆裡的大魚言之鑿鑿地說那就是”青魚”,或者說那些青綠色大魚的是”草青”,而傳說中的青黑色大魚是”烏青”,以此來把”草魚”和”青魚”攀上個親。 菜場裡只有”草魚”,與真正的”青魚”根本不是同一種魚。草魚小而青魚大,草魚吃素而青魚吃葷,草魚肉質粗糙鬆弛而青魚肉質緊實細密,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真正的”青魚”大概絕跡了吧,至少在菜場裡,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見過青魚了,既然如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改吃草魚吧。 雖然草魚肉質稍遜,但也不錯,至不濟肉多骨少,也很適宜老人孩子食用。既然草魚肉質欠缺,總要想點補救的辦法,鮮活是極重要的,上海講究”活殺”,若是一條”畢活鮮跳”的”草魚”,一條凍了多日的”青魚”,讓我選擇,我多半還是挑選前者。 除了死活之外,還有什麼?當然就是烹調了,清炒要用大油旺火一炒即起,最是考驗物料,所以清炒的話,弄不到青魚,就只能改用黑魚了。 熏魚吧,用油炸起來,再到糖醬油汗裡浸,可以掩蓋許多,再說熏魚吃的不是”嫩”,而是”酥”,草魚完全可以勝任。 還有什麼辦法?醃起來吃,醃過的魚統過”鹹魚”。魚肉經過醃製,會變成緊實,正好借過草魚的不足,倒是個很好的主意。只是醃魚很麻煩,據說殺了魚,取去肚腸後不能刮鱗不能洗,否則地話魚會發霉;以說醃魚不能曬,只能陰乾,否則魚會變臭;還說要勤趕蒼蠅,否則容易長蛆;甚至說要把魚掛得很高,否則會被貓咪叼走…… 反正,醃魚是件相當麻煩的事,不但有可能”吃力不討好”,還極有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我們要走一下捷徑了。 這回不說的草魚的具體醃法,留到以後醃海鰻的時候再說。好在就算自己不會醃,現在菜場的醃臘攤,都有現成真空包裝好的醃草魚賣。當然,包裝袋上也一定寫著”青魚”而非”草魚”。 包裝的魚段是透明袋子裝的,很漂亮,看著也都是中段,其實不然。這些包裝的袋子,很有蹊蹺,正面是透明的,反面印著說明之類,是不透明的,我就曾經買到過一段,打開袋子以後,發現魚段的背面藏著兩條魚尾巴,醃魚尾巴和雞肋差不多,沒什麼用。 可是,又不能把包裝拆開才買,看來只有使出”摸骨功”了,說實話,我摸不出來,但是你可以和攤主套近乎,他摸得出來。 其實,魚的部位還在其次,最主要的還是魚的質量,魚硬的,說得醃得透,若是在真空袋裡都感覺軟軟的,那麼打開袋子估計就是爛爛的了。另外,顏色也很講究,看魚皮是看不出花頭的,要看魚肉的切口,新鮮的醃魚,切口白色微紅,如果魚肉黃褐、暗戲,就是已經”耗”了的魚了。 鹹魚有許許多多的吃法,不同的鹹魚也有不同的做法,醃草魚可以蒸,當然,大多數鹹魚都可以蒸來吃,還過可以炒來吃的鹹魚不多,恰好醃草魚就可以。 醃草魚肉頭厚,又不是干得死硬,所以可以炒來吃,當然你不能整段魚都下鍋炒,要切成小塊來炒,塊的大小如骰子相仿,”骰”字在上海話裡發”投”字的音,所以就叫”投子塊”。將魚段平鋪,從背上切入,沿著腹骨”批”出魚肉,剔除魚骨。 然後就容易了,一大片的魚肉,先切條、再切塊,長短粗細要一致,切出來的魚粒,當然就漂亮。然而不能清炒鹹魚,那樣保證會咸死,總要找點東西來”借一借”,毛豆子就是個很好的選擇(關於毛豆子的細節,請參見拙撰《毛豆子炒醬瓜》),一份醃草魚,用兩到三份的毛豆子即可。 起油鍋,用大火將鹹魚粒爆一下,這樣的話,魚肉不易鬆散,將爆好的魚肉取出,放入毛豆翻炒。炒毛豆不是煮毛豆,煮毛豆只要放水煮,煮得爛酥即可,然而豆色變黃,賣相不行。炒毛豆用油用水用中火,水至少要毛豆的三分之二,要經常翻炒,才能保證毛豆又酥又綠。 待毛豆炒好,改用大火,收幹一部分水分,基本上讓剩下的水為毛豆的三分之一左右,將鹹魚粒倒入,剩下的水寧少毋多,水多的話,會把魚肉浸爛,影響口感。 放入鹹魚後,改用大火,炒到水份收干後,即可起鍋。由於醃草魚是鹹的,所以這道菜不用放鹽,依然咸鮮適口,是夏天”過泡飯”、”吃老酒”的好東西。 這道菜不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試,”批”下的魚骨和邊角料可以用來做湯,加點冬瓜同燒,也是消暑的恩物。
寫了一段時間的菜話,也算有了些讀者,他們往往會來問我一些小問題。我呢?也常常會說「想喫什麼?我明天寫給你!」他們就會說「你什麼時候燒一次給我們喫啊?」昨天,我又說了「想喫什麼?我明天寫給你!」結果,居然有兩個朋友都說要喫紅燒肉,我說「紅燒肉最容易了:肉放水中煮,煮熟加醬油,加糖就起鍋,到此就好了。」 紅燒肉真的這麼容易燒嗎?當然不是。否則為什麼衹有少數的幾家飯店有紅燒肉賣?有人說是因為紅燒肉「不上臺面」,所以店裡不賣。其實不是,這年頭鹹菜豬頭肉都上得臺面,還有什麼上不了臺面的?全是因為紅燒肉很難燒好,大多數飯店不敢砸了自己的牌子。 當年秘魯哲學家門德斯訪問中國,我們的毛老先生就請他喫過紅燒肉;當然,那是禦廚燒的。席間,毛老先生還說了如此的名言:「這是一道好菜,百喫不厭。有人卻不讚成我喫,認為脂肪太多,對身體不利,不讓我天天喫,只同意隔幾天喫一回,解解饞。這是清規戒律。革命者,對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麼脂肪呢!喫下去,綜合消化,轉化為大便,排瀉出去,就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怕什麼!」 前輩就是前輩,喫一頓紅燒肉,還能悟出革命的道理。我呢,則是燒紅燒肉,悟出了些心得,說出來給大家聽聽,也算拋磚引玉吧。 紅燒肉起碼有上百年的歷史,也起碼有上百種燒法,硬的,輭的,不輭不硬的;甜的,鹹的,淡的,甚至連辣的都有。最最好喫,最最好看,最最滋補卻最最不會發胖的,恐怕是蘇式紅燒肉了。 鄭逸梅老先生就是蘇州人,酷愛喫這道蘇式紅燒肉;乃至耄耋之年,步履維艱,仍愛喫肉。到後來,赴宴歸來,衹有一句話,要麼是「紅燒肉燒得滿好格」,要麼是「連紅燒肉也無沒」,滿桌雞鴨魚蝦,全不在眼中。 蘇式紅燒肉,當然源自蘇州;蘇州人燒菜,「做人家」佐料,著色並不厲害,但「濃油赤醬」四個字,是一定要用來形容蘇式紅燒肉的。肥而不膩、酥而不碎、甜而不粘、濃而不咸,這就是蘇式紅燒肉的特色。 這個紅燒肉嘛,挑肉最關鍵。肉要五花肉,蘇滬一帶叫做「肋條肉」,其實就是去骨的rib。肋條肉要挑夾精夾肥的,好的肋條肉可以夾上近十層,也叫「夾心肉」;品質差一點的,衹有夾四五層;再差一點的,一層皮,一層肥肉,一層瘦肉,就沒了。就算是差的肉,也有講究,要看是肥肉多,還是瘦肉多,如果是瘦肉多的話,尚可勉強;反之,則萬萬不能選用。前面說的那種十幾層的極品肋條,價錢要比大排、裡脊還貴;而且除非你認識攤主,隔天說好替你留著,否則一定要趕早;這種好東西,可是人見人愛的,而且據說一隻豬上,衹有兩條上好的肋條,加在一起,剛好燒一碗。五花肉,其實是豬身上營養最好的肉,西方人也非常喜歡喫,以至於喫到後來,就在去年的八月十二日,墨西哥對美國的五花肉要徵收百分之十的關稅,因為出口量實在太大了。有人說用臀尖肉,那衹是「醬油燒豬肉」,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紅燒肉。 肉不要買得太少,兩斤至三斤為佳。人少的話,也不能「按比例酌減」,這道菜,如果用半斤肉去燒,我敢保證,你絕對燒不好。要是人少一次喫不了,其實可以盛出來,放到冰箱中速凍,過幾天再喫。 肉要洗淨,切成麻將牌大小正方形的塊,肉不要切得太小,太小易縮易碎,沒有賣相了。切完後,用冷水浸沒,水中放半杯料酒。放在水中浸,可以浸去毛細血管中的血水;水中加酒易於肉纖維吸收,去除肉腥。肉不宜多浸,多浸則鮮味盡失,一般浸十五分鐘左右即可。 紅燒肉一菜,水最講究。水要一次放好,不要燒幹了,再加點水,有的書上說一小碗一小碗加,我試過,效果絕對沒有我的燒法好。就算萬一真的要加水,記得要加開水,切記,切記。我們要找一個大鍋,把肉再洗一遍後放入,水要浸沒肉,並高起兩寸以上。 有的人,做紅燒肉,先用油炸一遍,我好婆常說那是窮人家的燒法,肉經油一炸,不會縮但也不會酥,油走不掉,肉又硬,於是每個人就可以少喫幾塊。有的飯店也這麼燒,是因為這種燒法,時間短,樣子好,但說喫口,就不敢恭維了。 我要說的那道紅燒肉,是至醇至純的,不多任何一道不該有的手續,也不多放任何會引起「紅燒肉岐義」的調料。 鍋中加了水,就點火,火要開到最大,水中再放料酒,並且放半調羹醋。放醋可以讓肉質膨鬆,更容易燒酥;我的好婆放幹山楂,效果更好,香味更足,衹是不容易弄到。 大約五六分鐘後,水就開了,繼續煮上五六分鐘,隨著肉塊的翻滾,水面上會浮起一層黑紅色的雜質,這層雜質是燒熟的血水,上海人稱之為「琺」。這是上海話裡特有的一個字,沒有人知道怎麼寫,只知道應該念做「伐」。把這些雜質去掉,上海話裡也有個特定的詞,叫做「辟琺」,就是用調羹把雜質臽去的意思。「辟琺」並不容易,那些雜質會粘在調羹上。你需要事先準備一小碗冷水,每臽一下,就把調羹浸到冷水裡洗一下。「琺」要「辟」好幾次,鍋邊上粘著的,也要去除乾淨。 用大火滾煮半小時左右,可以改用小火,火的大小以水面不沸為準,叫做「焐」。焐呢,要焐至少一個小時,焐得時間越長,越好喫。紅燒肉,切忌旺火急燒,要的,就是這個慢功夫。你要時不時地去看一下,小心湯水被燒幹,當然,湯水燒幹也不見得是壞事。以前太倉城內南大街,有個叫倪德的廚師,就是因為沒掌握好火候,把紅燒肉燒得湯水盡幹,肥瘦分離,結果卻意外地發明瞭太倉肉鬆。 肉要燒得用筷輕戳可通,然後換到鐵炒鍋裡,開著蓋子燒。這時,要放醬油了,醬油放得太早,肉沾到鹽份便燒不酥,放得太晚,衹有外層的肉被染上色,不能入味。火呢,要比剛才「焐」的時候大一點,但也不用開得極大,因為現在肉已爛了,火開得太大,會把肉煮碎。 醬油要選色深但不是太鹹的,廣東菜裡分老抽和生抽,老抽其實是放了焦糖的,我們要的就是這種;生抽呢,則是色淡味咸,不能用。做蘇滬菜,其實完全可以用上海醬油,有個叫「海鷗特濃醬油」的,就不錯。 這樣,再煮上半個小時,鍋裡的水就差不多了,此時,我們要放糖了。糖,要敢放,要捨得放。糖的數量,大約一斤肉一兩糖,糖最好用冰糖,冰糖甜度高,味純,透明度也高,乃是燒這道菜的關鍵。冰糖塊大,要事先敲碎。 放糖的時候,火要開大,放入糖後,湯水會慢慢地厚起來,可以輕輕地翻動肉塊,如果怕自己水平不行,擔心把肉塊翻破的壞,可以用勺子將湯水臽起,再澆下去。糖放入後,湯水很快就可以收幹,所以千萬不要離開,如果香味實在誘人,可以蘸一點湯水先解解饞。等到湯水變得更加稠厚,有油亮泛起來,這道菜就燒好了,湯不用燒得太幹,紅燒肉湯拌飯,乃是天下極品。 這便是正宗的蘇式紅燒肉,除酒、醋、醬油和糖之外,全無其它調料佐料,是謂原汁原味。有的飯店,先用油炸,再加薑、加茴香、加醬油炒,然後加糖,再用澱粉著膩,撒上蔥花就算好了。這種紅燒肉,十五分鐘就可搞定,但是喫一塊就倒胃口,真是大丟紅燒肉的臉;而且,這種紅燒肉定會喫得你口幹舌燥,腸胃不適;奉勸大家不要嘗試。
有樣東西,是取一隻碗,放入一個生雞蛋,再加點水,攪打均勻後放些鹽,然後放在鍋裡蒸,起鍋後,是一碗滾燙的如果凍般的東西。各地對這種食物的叫法各不相同,南方以「蒸蛋」或「蒸雞蛋」為主,北方則以「雞蛋羹」、「雞蛋膏」或「雞蛋糕」居多。這件東西,還是上海人叫得最有神韻——「燉蛋湯」。 如此簡單的東西,還值得拿來說?其實,比物之難,遠勝於炒青菜。而且,難就難在炒青菜如果咸了,下回少放點鹽就是了,可以此物要是一回失敗,簡直會次次失敗。 最常見的失敗有兩種。第一種是水蛋分離,上面有一層蛋,舀破表面,下面是水,常有人覺得是沒有蒸熟,於是下回就增加時間;也有人覺得是水加多了,就在下次調整比例。這樣的做法,導致了第二次失敗的產生——蒸得太老,蛋體太厚有空洞,於是便再調整時間和蛋水的比例。然而,蛋、水和時間,彷彿故意搗亂,永遠也摸不透它們的規律;失敗也總是在兩種形式中徘徊,怎麼也找不到一個中心點。 還是要說到上海話,衹有理解了「燉蛋湯」一個字,才能做好這道菜。首先,是「燉」字,原來這玩意不是蒸的,急火旺蒸、受熱不均,是此菜大忌。先要準備一個鍋子,想法把碗架起來,不要讓碗直接接觸鍋底,然後放水,水的高低以稍低於碗沿為準。目的,就是要水多蒸汽少,所以是燉不是蒸。將碗取出,開火燒水。 燒水的時候,可以調弄一下「湯」了。明明是固體,為什麼叫湯?這就是此菜的精華了,燉蛋要燉得極嫩才好,似湯非湯方才達到境界。蛋,放入碗中,用筷子搗散,有人喜歡端點碗攪打,但容易產生許多泡泡,影響美觀;若是用西式的叉攪拌,效果更好。另外還要加水,水要七十度左右的熱水,加一點,攪幾下,再加一點,再攪幾下;水加得越多,蛋越嫩,大概的量是一隻蛋加一玻璃杯水,另外,不要忘了放入鹽和料酒。 蛋,一攪好就要蒸,靜置時間一長,易分層,蒸之前,用勺舀盡浮沫,再覆以保鮮膜,以免蒸汽冷凝滴落和開水溢入。將火關小,小到水面不動為止,放入盛有蛋液的碗。然後,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過程,要多少時間?半個小時。 如此製作,等到取出燉蛋,保證你會「驚嘆」自己的手藝,用幼嫩水滑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燉蛋,還可以做成甜的,放入冰箱冷藏後再喫;也可以取文蛤肉放入,用煮文蛤的水打蛋,其味鮮美異常,甚至有人認為文蛤燉蛋,是蛋中的至高境界。

你好!
祝賀出書!
自詡老饕,多交流。
王沛仁老饕說吃: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2342824_5_1.html
你好!
祝賀出書!
自詡老饕,多交流。
王沛仁老饕說吃: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2342824_5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