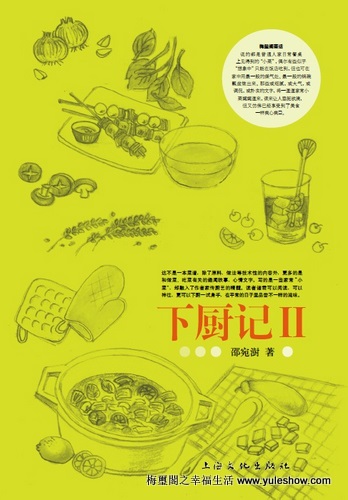
茲定於《下廚記 II》於2011年上海書展首發,簽售會定於8月21日中午11:15,會後將有AA制午餐會,想參會的朋友請私信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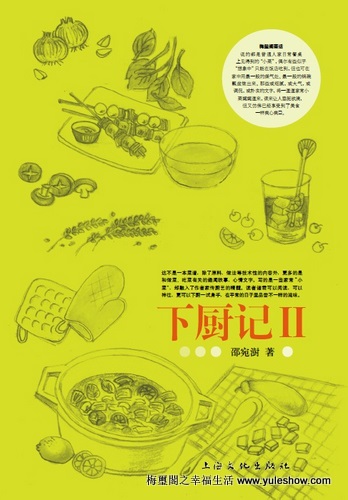
茲定於《下廚記 II》於2011年上海書展首發,簽售會定於8月21日中午11:15,會後將有AA制午餐會,想參會的朋友請私信報名。
茄子,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植物。在南方,它是長長的、細細的,越往北去,它就越粗越短,到得最後,竟然變成了一個圓球,造物主的神奇,便在於此。 茄子的英文叫做eggplant,以前總是背不出,直到看見茄子植株,不禁開懷大笑,原來,那茄子的花是雪白的花瓣圍著一朵嫩黃的花心,遠遠地望去,與對半切開的水煮雞蛋並不二致,天下居然有如此奇物,不旦好喫,還能幫我背出單詞,真是令人開心。 老式的上海話中沒有「茄子」一詞,衹有「落蘇」。說起這詞,還有一個笑話,說是有外國友人到上海某農場去參觀,一個老農說到「這是茄子」,於是翻譯便譯作「eggplant」,那老公隨後又說那又叫「落蘇」,這下難倒翻譯,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說那玩意又叫「plant of egg」。 笑話歸笑話,這落蘇一詞,可是大有來歷呢。《本草綱目》中有記載:「茄,一名落蘇,名義未詳;按《五代貽子錄》作酪酥,蓋以其味如酪酥也,於義似通。」 上海話中衹有「落蘇」,並不是說別的地方不說「落蘇」,別的地方不但也叫「落蘇」,而且還有「落蘇節」呢。七月三十日,是地藏王菩薩的生日,小朋友便極喜歡這個節,因為這天可以玩「落蘇燈」。落蘇燈,是在茄子當中挖個洞,裡面插上小蠟燭,與那西方鬼節的「南瓜燈」有異曲同工之炒。孩子們便舉著落蘇燈,比落蘇的大小,比蠟燭的明暗,可以玩上一整夜呢。至於茄子當中挖洞放蠟燭,想來必要那圓圓胖胖的茄子才行。 茄子不但好玩,而且好喫,貌不起色的茄子,卻可以做出各式精美菜餚。光是素做的,就有涼拌茄絲、清蒸茄片、熱炒茄段,素菜館裡甚至還用茄子批成薄片,外裹生粉、麵粉、胡椒和辣椒,再漬以醬油,經油炸而成一道「素鱔背」,其喫口與味道,幾可亂真,可謂天廚炒手。茄子或是葷做,多半也是唱主角,如那「茄子煲」一味,便是茄子為主、肉糜為輔;至於《石頭記》中的茄鯗,更是把這人間美味發揮到了極致。 茄子,還是食補佳材,其性涼、味甘,具有清熱、解毒、活血、止痛、利尿、消腫等功效。茄子的營養價植相當高,含鐵、鈣及維生素A、B、C等,而且紫色的茄子還富還維生素P,維生素P可以增加人體細胞的粘著力,增加血管彈性,降低血管脆性並且防止微血管破裂出血,可以預防壞血症並且可以幫助癒合傷口,對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紫斑病等都有一定的治療和預防作用。 我們今天的這道「茄夾」,又名「茄盒」,可葷可素,可簡可繁。這道菜,金黃鮮亮,脆嫩適口,一口咬上去,更是有熱氣噴出,茄香四溢,每當茄夾上桌,大家往往舉著如飛,霎那間,便可喫個盆底朝天,可見此菜之鮮美。 做菜,先要買菜,再是洗菜,萬事都得用心才行;要做得好菜,非常有那份耐心。茄子,宜買嫩的,嫩的茄子,皮亦可食,而茄子皮則又是茄子中營養最好的部分。新鮮的嫩茄子,表皮光滑,無褶皺,顏色鮮亮,呈淡紫色,為上品;而不新鮮的,則呈深紫色。若是兩種茄子放在一起,有天壤之別。茄子不能挑太粗的,粗的茄子有籽且老。若是仔細觀察,可以看到茄子頂部有片果萼,那兒有一個淺色的圈,那個圈越寬、越明顯,則說明茄子正在快速成長,定然鮮嫩;如果那個圈不明顯,就表示茄子已經長過頭了,裡面還會有硬籽,大大影響食用。做這道菜,如果選用那種長茄子,還要注意儘量挑選長一點、直一點的,否則切不出長片來,會浪費許多。 茄子買來後洗淨,切片,切片時要注意斜著切可以使茄子片大一點,做出的茄夾更漂亮。地道的做法是在兩片茄子的當中放上餡料,做出的茄子厚薄均勻。也有的人偷懶,切一片厚點的茄子,當中豁一刀,塞入餡料,衹是喫的時候,衹有一邊有餡。茄子切好後,極易氧化,在表面產生黑色的小點,衹要用鹽水輕輕揉洗,就可去除。 另外的工作,其實可以在切茄子之前,先做好。其一是拌餡料,最簡單的是用肉醬,放點生粉、鹽和料酒,拌勻即可,生粉既可使肉鮮嫩,還可提高附著力。若是喫素的朋友,可以用烤夫和藕丁拌和,比用肉糜,更加馨香。講究的做法,更有放入海參和蝦仁的。 還有一道工序,是要調配裹漿,用蛋和麵粉拌勻即可,麵粉中要放點鹽,但不要太多,麵粉漿厚薄隨意,總以能夠沾上茄子裹住為準。 在一片茄子上放上餡料,用手按緊,防止其掉下,再覆上一片茄子,同樣按緊,裹上漿料,放油裡炸一下,等到外面的漿料不流動,就取出,等所有的茄夾都炸過一遍,再一起放入油炸,等顏色變成金黃,就可以裝盆上桌。 食用時,可以蘸番茄沙司或者椒鹽,都各有風味。茄夾一定要趁熱喫,因為茄子水份豐富,外面的殼易軟, 便沒有嚼頭了。 另外,有些大廚製作,只用一片茄子,上覆餡料,不裹漿,直接油炸而成;衹是那種做法,餡料難調,油炸更為不易,大多數人不肯製作。
今天讀了一篇科普文章,說的是中子星,從頭到底,衹看懂二句話,一句是「中子星有二十個太陽那麼重,卻衹有一個城市那麼大」,另一句是「一個乒乓球大小的中子星物質,有十億噸那麼重」…… 這篇文章並不討論中子星,我想說的是太陽,太陽的光,陽光。加州的陽光,向來有名,特別是南加州,沙灘,陽光。說到南加州的陽光,有個笑話,我聽說這個笑話有十幾年了,說是有位內地的官員,睦名到洛杉磯,特地要去沙灘去曬曬太陽,入境的時候,移民官問他到美國來幹嘛,那位官員想說是為了「sun of the beach(沙灘的太陽)」來的,結果他的英語實在口音太重,說成了是為了「son of the bitch(狗娘養的)」而來,閙了個大笑話。 南加州的陽光,真的很漂亮,也很厲害,但凡中午的時候,一年四季皆可單衣短袖,噢,不,一年二季,一季很熱,一季熱。不過今年很奇怪,現在是七月中旬,要照往年,已經大熱了二三個月了,中午的時候,怎麼也要超過三十八度了,攝氏三十八度是華氏一百度,這裡的人就稱為「三位數的氣溫」了。 今年,在過去的一百天裡,一大早起來就看得到藍天的,大概衹有十五天,其它的日子都是陰陰的,甚至有連著一週沒出太陽的,讓人想起上海的黃梅天來。今天的夏天太陽不旺,自然氣溫也就不高了,我一個朋友舉家來洛杉磯玩,一下機場後悔衣服帶少了,想像一下,在洛杉磯的夏天,覺得衣服不夠,是該有多冷,這可是洛杉磯不是舊金山,因為有句話叫做「我經歷過最冷的冬天,是夏天的舊金山」。 太陽不正常,地球也就不正常,這不洛杉磯大震了三次,第一次是橫著搖,頭暈暈的;第三次是上下搖,一點也不害怕,衹覺得有趣,家中的貓更是躺著動也不動,第二次的時候,大家都躺著睡著了,誰也不知道。不但洛杉磯大震,華盛頓特區還下了場特大的暴雨,連白宮的媒體休息室都給淹了。 好在這幾天,大陽正常了,洛杉磯也熱了起來,車子在太陽下停一會兒,再上車就連方向盤都燙得摸不上手了。 天熱了,小豆子鬱悶了。 小豆子是我的女兒,長期讀我書的讀者應該知道。小豆子已經不小了,已經大到學開車了,在美國學車很容易,我會在《加州小事》中詳細講述。那天,小豆子練車,我陪她,一路開啊開,從帕薩迪納開到哈仙達崗,我正好去99大華買點菜,就在收銀檯前,小豆子看到了一種日本產的夾心巧克力豆,她小時候在上海很喜歡喫這種巧克力,於是隨手買了一罐。 買好東西,放在後備箱中,回到家中,拿出東西來,小豆子拿起巧克力,就開始鬱悶了。那種巧克力,是一個大大的細硬紙管,小豆子拿在手裡,一搖,什麼聲音都沒有。 「咦,怎麼沒聲音呀?」小豆子說。 「沒聲音怎麼啦?」 「搖不響說明化啦!」小豆子一臉鬱悶。 打開一看,巧克力豆全化了,一團糟,衹能扔了。 第二天,又帶著小豆子練車,這回開到了西科維納,在日本超市喫了午飯後又去香港廣場買維他檸檬茶,這家超市也有那種巧克力賣,這回小豆子不鬱悶了。 在香港廣場,小豆子看到塊牌子,寫著「龍躉魚」,問我這個「躉」是怎麼念,我記得廣東話是念「膽」的,許多店中不會寫「躉」,菜單上不就寫作「龍膽魚」麼?我告訴小豆,應該唸作「膽」,還告訴她,就是「一百條百腳」,一百乘一百,沒毛病。 買了一爿大大的龍躉魚頭,為什麼是「爿」?因為是半隻魚頭,對剖的半個。回了家,沒急著弄魚頭,先幹了件壞事。 這天在日本超市買了生蠔,盛了很多冰,後來在香港超市買好巧克力,當場搖過是有聲音的,然後就和生蠔放在一起,到家就沒問題了。小豆子一到家,沒來得及馬上喫巧克力,我趁她不注意,把管中的巧克力豆倒在一個自封袋裡,藏好;然後又把COSTCO的提子乾巧克力豆裝在那個紙管中,然後開始弄魚頭。 龍躉魚的魚頭很大,買好就讓店裡給劈開了,劈成了八塊,我打算洗洗乾淨,然後喫一半凍一半。一洗,發現問題了,魚頭上有很小的鱗,刮又刮不下來,我有把挺大的鉗子,是用來做去骨魚拔魚背的刺用的,於是夾著魚鱗往下扯,沒想到小小的一個魚鱗,拔出來之後,是長的一條。這個魚鱗很奇怪,不是圓的而是長的,也不是一片片疊在一起的,而是一條條長到魚皮中的,藏在魚皮中的部分倒有露在外面的四五倍長。 八塊魚頭,有三四塊都有小鱗,用鉗子「拔」了半天,心想好不容易收拾好了,再一看,鰓蓋上也有鱗,而且是完全在魚皮之下的,連個尖都沒露出來。這回麻煩了,好在頂層的魚皮不厚,用鉗子可以隔著魚皮夾住魚鱗,然後用力扯出來,這回的鱗倒是半圓形的。 我還在「扯」魚鱗,小豆子又鬱悶了,能不鬱悶嗎?這巧克力完全不是小時候的味道啊! 我實在忍不住了,又不能捂著肚子笑,手上腥著呢!小豆子發現我不對勁,不等她逼問,我就招了。 我也發現我讀錯字了,這個字不就是「擁躉」的「躉」嗎?那應該唸作「盹」才對,告訴小豆子,她還沒笑停呢。 繼續扯魚鱗,半隻魚頭,前前後後弄了一個小時左右,方才弄得乾乾淨淨,想想當天菜多,就都放在凍庫中了。 第二天,取出化凍,待得化開,大喫一驚。昨天去鱗的時候,絲毫不腥,及至凍了一夜再化開,居然奇腥無比,怎麼會這樣?…
煲仔飯,我肯定是寫過的,因為我為了煲仔飯,燒壞過一個砂鍋,那件事太令我沮喪了,我居然把砂鍋都燒爆了,真是丟臉。在那以後,在追索煲仔飯的道路上,我發現了「高溫煲」,也發現了「防風網」,二件東西組合起來,燒煲仔飯太方便了。 我離開上海的時候,沒有帶著高溫煲和防風網,我不是一向號稱「一刀一鍋走天下」的嗎?那我不能帶炒鍋之外的鍋呀!其實,我一個鍋也沒帶,這都什麼年代了,出國還帶鍋?至少也得是個電飯煲吧?又能燒飯又能煮麵的!不過,我也沒帶電飯鍋,我又不是廣東人出國旅遊,這年頭,還怕沒有鍋用?當年侯凱蒂女士就在舊金山的家中使用廣東炒鍋了,這又十來年過去了,相信一定會更方便的。 果然,第一天,我就有鍋了。那是洛杉磯親戚用的「歡迎套餐」,或者稱作「落地套餐」,有幾個盆子,幾個碗,幾個料理盒,一個電飯煲,幾雙筷子,幾把調羹,幾副刀叉,一小袋米,以及二套鍋子。 合著這位親戚就打算讓我們自己煮白飯喫,你好歹也送個三百斤牛排二百隻龍蝦過來吧?我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兒買菜去?說笑話啦,我第一天就做了鹹菜肉絲麵喫了,還怕難得了我? 事實上,我差點被那位親戚難死! 她送我的二套鍋子,一套是十幾件的鋁製不粘鍋,美國人說的十幾件,鍋蓋和鍋子是算二件的,再加把炒勺又是一件,所以十幾件鍋具,總共也就三套大中小的鍋子吧;另外一套,是砂鍋,一個大的可以燉雞湯的砂鍋,一個小的,和煲仔飯砂鍋差不多的大小,衹是要深一些。 可是!可是!我沒法用這二套鍋子!因為我是電磁灶,一個帶烤箱的四眼電磁灶。對了,如果大家最近要買灶頭的話,我強烈推薦大家用電磁灶。很多年以前,上海人開始在家裡喫火鍋,就買一隻單個的電磁灶,那玩意非常不好用,常常是把肉片放下去之後,原本滾著的湯不動了,要等它慢慢被焐熟才能喫,你想呀,會好喫嗎?但那是老皇曆啦,不用擔心新式電磁灶的火力不夠,我親測實用,比煤氣加熱要快,因為電磁加熱,沒有「野火」,熱效率更高,而且,整個灶臺就一塊平板,清理打掃特別方便。別再迷信煤氣爐啦,除非你像我一樣使用可以加風的炮臺,普通家用的話,電磁灶比煤氣灶不知方便多少。 什麼?你要用中式圓底炒鍋?有二個辦法,一種是買塊專門配圓底炒鍋的電磁板,放在電磁灶上,再把炒鍋放在上面;還有種就是出很多很多錢,買德國某著名家電品牌的電磁灶,他們的電磁灶有一個眼是凹下去的,專門配他們的圓底中式炒鍋,好吧好吧,看在他們曾經逢年過節就送我禮物的面上,我就公佈一下他們的品牌吧,叫做「美諾」,英文名是「Miele」。不過,我不是托,我衹是知道他們有這個產品,雖然我在他們的展示廳做過展示,但我衹用過他們的平底電磁灶,沒有用過那個凹下去的炒鍋,所以到底效果如何,我可不作任何承諾哦! 我沒法用砂鍋,也沒法用鋁鍋,雖然可以買塊鐵板放在電磁灶上,但我實在沒有興趣架床疊屋,我選擇另買幾口電磁灶可以用的鐵鍋。炒鍋是在日本超市買的單柄熟鐵半圓平底鍋,很稱手,份量和大小,都滿意;燉鍋是在梅西百貨買的二口鑄鐵鍋,Martha Stewart牌的,大的打完折八十九美元,小的才三十九,我可不買酷彩,我這人不注意保養,好東西到我手裡沒用,我又不是器材黨。 那口小的鑄鐵鍋,用來做煲仔飯,正好!開口和煲仔飯的煲差不用,深度同樣是二倍左右,二三口之家,一鍋正好,我要做道板鴨煲仔飯。 美國也有板鴨?有啊,我在洛杉磯,什麼沒有啊?活的大閘蟹都有,朋友圈就有人賣,二十美元一個;茭白也有,七美元一磅,好運來超市有……除此之外,讓我仔細想想,豆腐品種比上海多,鮮筍品種比上海多,好像除了草頭沒有之外,別的都有。 對了,沒有五芳齋大肉粽,衹有五芳齋赤豆粽、豆沙粽;所有豬肉製品,都是美國本土生產的,因為豬肉不能進口嘛!中國品牌的食品,好像在美國建廠生產的還不多,反正我印象中是一個都沒有。至於港臺,有很多牌子有廠家,李錦記是美國本土生產的,味全的速凍食品,從水餃到餛飩到各式包子,都是本土生產,我買的板鴨,也是美國生產的。 板鴨,就是鹹鴨,所以上海人也稱之為「鹹板鴨」,要注意的是,鹹鴨蛋並不是鹹鴨生的!板鴨是用鹽和香料炒過之後,經過乾醃、滷醃以及用鹽纍胚後晾乾而成的,工藝相當複雜,不建議各位自力更生,我向來主張,買得到且品質好的,不必自己做。 能不能用臘鴨做?當然可以,臘鴨和板鴨的最大區別,在於形狀,臘鴨是「鴨形」的,板鴨是「板形」的,後者開膛後在纍胚過程中被鹽的重量壓扁了,成了平平的一張,象塊板似的,故有此名。 我買到的板鴨品質相當好,生的時候聞著就有香味,絲毫沒有油氣;問題是質量太好了,水份醃得太乾了,生的時候,鴨身不過半釐米的厚度,我得想法讓它還個陽。 一隻鴨子太大了,半隻被我春節時做手撕板鴨時用掉了,剩下的半隻,被我一切二,成了二塊,放在碗中疊起來。我除了炒鍋鑄鐵鍋,還有蒸鍋呢,誰標榜自己一鍋走天下來著?我的意思是一個炒鍋啦!第一次看到寫文章寫能跟自己吵起來的!我在譯作中還以譯者身份和原作者對罵呢! 蒸,放在碗裡隔水蒸,包裝上寫蒸十五分鐘,千萬不要上當,別說十五分鐘,十個五分鐘都不夠,十個十五分鐘也不夠。你說蒸了二個半小時,能不能喫?能喫,但挺費牙,練練咬嚼倒是不錯。好的板鴨,要喫口微鹹,咬口軟糯,才是上品,記住,要糯,糯的前提,就是要厚實,哪怕是糯米,一片小薄片是感覚不到糯的,衹有大口咬大塊,才能體會。 我蒸了四個多小時,眼瞅著它慢慢變厚,最終「漲發」了有四五倍之多,完完全全「象」一隻鴨子而非塊「板」了。 在三個多小時的,我舀了三小罐米,電飯煲的罐,放到了鑄鐵鍋中,淘洗乾淨後,放水浸著。等到板鴨蒸好,我把浸米的水倒去,把蒸鴨碗中的湯汁潷到鑄鐵鍋中。 用板鴨的湯汁燒飯?是的,那樣就用醬油也省了。 會不會太鹹?實測三罐米,蒸四個半小時的湯汁,不鹹。 會不會腥?有可能,所以要用薑啊! 我事先準備了一塊薑,扦去了皮,先切片,再切絲,倒也不少,別把薑拌在米裡一起燒,那成薑燒飯了。 湯水倒下去,正好與米齊平,那就還得添點清水,高出米面一指節不到點的樣子。開火燒,最大的火,直接燒,在一旁等著,鍋小米少,一會兒水就開了,雖然鑄鐵鍋蓋重,依然會有熱氣冒出來,鍋蓋輕微跳動,看著很開心。 動靜會突然小下來,大概五六分鐘的樣子,開蓋,米脹胖了些,米面上面還有水,這時撒上薑絲,我還切了二根潤腸放在半熟的飯上。潤腸是加了鴨肝的豬肉香腸,美國也有賣,記住,潤腸衹能厚切,否則會碎成渣,我用的是斜刀,讓潤腸更大一些,咬嚼更有快感。 看清楚了,薑絲不是一開始就下的,等米脹開才下的,衹是撒在表面,就夠了,不喜歡喫的,可以一下子撥開。這時,火調到了最小的火,鑄鐵鍋這點好,蓄熱量大,即便是最小的火,可它的底部還是很均勻地熱著,正好適合燒煲仔飯。 燜十五分鐘左右,其間什麼都不用管,時間差不多開鍋,米飯已經好了,這時,鑊焦,也就是底上的鍋巴,還沒有形成,淋一大調羹的油下去,同時把火調到最大,等聲音起來之後,燒二到三分鐘即可,保證有一層鍋巴。 第一,考的是耐心,十五分鐘,不翻不動不開蓋,就讓它慢慢烘著,要敢;第二,考的是膽量,油下去後,最大火,二三分鐘,不翻不動不開蓋,就讓它火急火燎地燒著,要敢。怎一個「敢」字了得。 這時的板鴨,大骨一扯就掉了,把板鴨放在砧板上,用刀壓住,拍刀背來切,否則鴨肉易散,當然前提是把快刀,用鈍刀,怎麼都會弄散的。把切好的板鴨,放到煲仔飯上,燜一會兒。…

你好!
祝賀出書!
自詡老饕,多交流。
王沛仁老饕說吃: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2342824_5_1.html
你好!
祝賀出書!
自詡老饕,多交流。
王沛仁老饕說吃: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2342824_5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