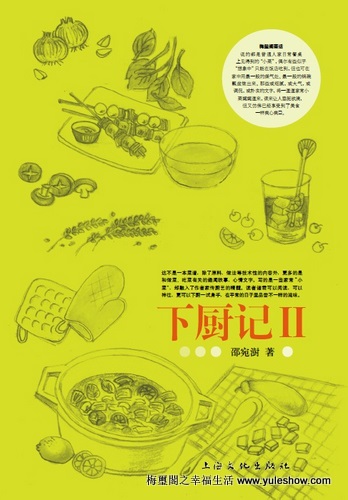
茲定於《下廚記 II》於2011年上海書展首發,簽售會定於8月21日中午11:15,會後將有AA制午餐會,想參會的朋友請私信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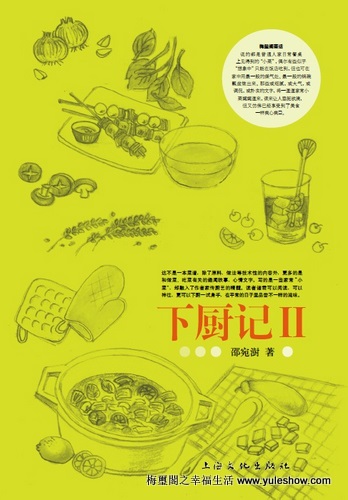
茲定於《下廚記 II》於2011年上海書展首發,簽售會定於8月21日中午11:15,會後將有AA制午餐會,想參會的朋友請私信報名。
經常有人問我,說是上海的福記怎麼樣,福記港式茶粥麵。前段時間,有人寫了篇說福記不好的貼子,說是福記的廚師還是老闆不戴廚師帽什麼的,也沒仔細看,然後就有一眾起鬨的,好像逮到了天大的把柄似的。什麼耳光餛飩什麼長腳麵,廚師別說帽子了,有時連衣服都不穿呢,那些人不照樣喫得開開心心?跑到這裡沒戴廚師帽就是個事了?告訴你,在中國,醫生不戴手套都很多,別說廚師戴帽了。再說了,上海有法律廚師必須戴帽子? 對我來說,在基本的衛生之外,衹要廚師好喫以及老闆是個好人,就可以了。這不是說我喫一家店要搞清楚老闆是好是壞,我的意思是如果知道了老闆是個壞人,那我就不會去那家店喫了,哪怕味道再好。我哪天開了飯店,一定會有人堅決不到我店裡喫的,我在有些人眼裡就是壞人;這也正常,天下人的三觀不可能都一樣。 福記的老闆,就是老闆娘,就是朱姐。她是不是好人?我告訴大家一個判定老闆是好人壤人的訣竅:那就是店中員工是不是象走馬燈一樣換人,換得越勤,老闆越壞。你想呀,飲食行業是人員流動很快的地方,如果一家店一直用著老員工,老闆一定不會錯的,不但要工資合適,還要管理有方,有態度而沒脾氣。 至於從不換員工的飯店,要麼是家庭飯店,是麼是賣蒙漢藥的黑店。 福記的員工都是老員工,採購的、端菜的、後廚的、打掃的,常客應該都有點面熟陌生。如果一家老是換員工,衹有老闆才認得出常客,那家店開不好的。是的,福記有時會有一個二個姑娘突然不見了,後來也沒再見,那是她們回潮州鄉下結婚去了,不是被朱姐賣掉了,她們中有些等生了孩子會再來的。 福記的東西,大多數挺好喫的。為什麼說大多數?記住,如果有人說某家店每一樣都很好喫,要麼這家店衹賣二三樣東西,要麼是個沒見識的,最大的可能,那是個托(拿錢的美食評論家)。 我們說的是一家賣幾十種上百種菜點的店,牽扯到的食材更多,不同的渠道進貨,不同的準備和烹調,不可能每道都好喫的,總有主打次打的,你也不可能一天廿四小時狀態都是一樣的吧?對於上百道菜點都要好喫,都受到同樣的歡迎,要比廿四個鐘頭一直high著都難。一家飯店,有幾個招牌菜是業中最好的,那就可以生存下去了,要是有個十來個,那就很招同行忌了;大多數好喫,對我來說,是件不得了的事。 而且人的口味,也是有區別的,我就和人不一樣。福記的著名豬排,從創意從選料從醃製從烹調從裝盤來看,都是很好的,但我就是不喜歡;我衹說了「從」沒說「到」,應該說「到蘸料」,福記是不配辣醬油的,對於一個上海人來說,炸豬排就不能沒有辣醬油。然而福記的豬排配了辣醬油的話,你會發現不但對辣醬油陌生了,就是連豬都陌生起來。 福記的炸豬排,不是我的菜。然而蝦仁滑蛋、甘蔗鴨、豬頸肉,都很好喫;特別是臘味生炒糯米飯、乾炒牛河,在我還沒有港式炮臺的時候,想喫這二道,還衹有去福記喫。再有港式奶菜,福記的奶茶是上海市售奶茶中最好喝的;為什麼說市售?因為我還有位兄弟做的奶茶是全上海最好喝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茶業生產和經銷商的僱員,整天就是研究奶茶。有人說,福記的奶茶在香港隨便找一家都行,但問題是,你在上海出錢能買到的最好的港式奶茶,就在福記;我曾經喝過網紅的靜安別墅奶茶和其它幾家上海港式茶餐廳的奶茶,都不能和福記比。福記的奶茶,要記得一點,別在晚上喝,喝多了睡不著。 要是問我,福記什麼最好喫?我的回答是:豬排檬粉不要豬排。聽上去像是「大腸麵加大腸不要麵」的反面吧?是的,豬排檬粉不要豬排。你如果曾經看到我拎著一個打包罐走出福記,那就是打包了一份沒有豬排的檬粉。不要以為我有多闊氣,買了東西把豬排扔了,我在福記喫東西是不付錢的。 為什麼?我面子大! 福記最讓我懷念的,就是檬粉了。現在到了美國,我衹能自己做。 先來說一下檬粉是什麼,我在福記喫檬粉,朱姐總是個我幾瓣小青檸,菓肉綠色的那種,我一度以為檬粉就是「配檸檬的冷米粉」。 當然不是的! 「檬」,就是「米粉」,是越南話「Bún」的音譯,指圓的細的米粉,與廣西的米粉雲南的米線,都是同樣的東西;衹是後者常是新鮮的,在除了越南本土和洛杉磯之外的地方,「檬」都是乾的。 檬粉完全可以用乾的來做,雖然洛杉磯買得到新鮮的,但那得到小西貢去買,偷懶或者不偷懶的話,到亞洲超市買乾的就是了。說偷懶是因為偷懶不開車,說不偷懶是因為新鮮買來衹要加魚露就能喫,否則就得自己煮了。 亞洲超市都有檬粉賣,或者說越南粉。「Bún」有二種,一種是熱食的,也就是「湯檬」,一般寫作「Bún bò Huế」,是「順化牛肉粉」的意思;還有一種就是做冷食的檬,包裝上經常寫成「Bún tươi đặc biệt」,是「特製新鮮米粉」的意思。熱食粉與冷食粉最大的區別是後者要較前者為細,更容易沾上調味。 調味,對的,越南、廣西、雲南,乃至貴州、江西、廣東,在粉上的區別是調味的不同(成分稍有不同)。 讓我們先把檬粉煮上。大多數檬粉,是放一大鍋水,待水沸後放入乾的檬粉煮五分鐘,再在水中焐二分鐘,然後過冷河。在關火之前咬一下,要沒有硬芯才行。我曾經買到過一種袋上說衹要燒五分鐘的湯檬,燒了廿分鐘後芯還是硬的。 細的檬粉,一下水,水就會變得很混濁,五分鐘之後,簡直就是一鍋稀一點的漿糊。過冷河的意思是浸在冷水裡,具體的操作法可以把鍋放在水斗中,用冷水沖淋。不要嘗試用筷子挾點起來放在瀘網裡沖,還不到時候,現在還是一糰糊,用筷子挾的話,首先挾不起多少,又滑又重,而且還很容易斷。 放冷水,用筷子沿鍋壁攪動,待水滿了,倒去半鍋,繼續,直到湯色變清,這時檬粉也不黏在一起了。這時也不燙了,直接用手抓一把放在瀘網中,在水籠下衝洗到冷透。什麼?我怎麼拿手抓檬粉?是的,我還沒戴廚師帽呢。 沖洗好的檬粉,放在另一個容器中,再從鍋中抓一把出來洗,直到全都洗淨。與麵條不同的是,洗淨的檬粉不會黏在一起。 要調一個汁,越南檬粉要照越南的風味調,關鍵是魚露。先用溫水兌一點糖,最好是越南黃糖,沒有的話,白糖也成;待糖化開,放米醋和魚露,擠點青擰汁,然後放入新鮮的薑片與蒜片,剪一二個越南小紅尖椒下去。有人是切蒜蓉擦薑茸的,我不喜歡,那樣有雜質感,我喜歡用薑片蒜片浸泡,最後用篩網濾一下,清清爽爽的調汁。 切一點生菜絲墊在碗底,再抓點綠豆芽,對的,生的,綠豆芽沒豆腥,可以生喫;再放幾片新鮮檸檬葉,沒有就算了,有就放點,沒有也不值得特地買。抓把檬粉在碗中,撒點花生碎,一碗沒有豬排的檬粉就做好了;調汁跟著上桌,想要多少自己放;調汁要甜不要鹹,跟純的魚露和青檸一起上,有人嫌淡可以自己加魚露或青檸,調汁有個專門的詞,叫「渃蘸」。 這是基本的冷食檬粉,上面放燒肉,就是燒肉檬,放春捲,就是春捲檬;要是放一塊紅燒大排,那就是融合菜:叫做「上海大排越南檬」。…
黃瓜的品種很多,上海人喜歡喫「本地黃瓜」,本地黃瓜又以淞江九亭出產的為最好。本地黃瓜顏色較濘,比較細長且表皮粗糙,外地黃瓜呈黃綠色,個子矮胖,籽多肉爛,不好喫;特別是涼拌黃瓜,一定要用上海本地黃瓜。黃瓜當然也是越新鮮越好,新鮮的本地黃瓜表面有硬硬的刺,摸上去有紮手的感覺,除此之外,新鮮的黃瓜上一朵嫩黃色的花,存放時間久了,那朵花會淍落,成了真正的「昨日黃花」。 黃瓜入菜,涼拌是一大喫法,印度菜中,將黃瓜、番茄切成塊,拌菜泥而成印式色拉;新疆菜中將黃瓜切片,番茄切條,加上生洋蔥絲,拌以白醋而成維式色拉,又叫「老虎菜」。東北人則說新疆沒老虎,這老虎菜應是他們的。 上海的涼拌黃瓜更簡易一些,將黃瓜去頭切尾,對半剖開,用菜刀的刮去裡面的籽,然後將黃瓜皮朝上橫放在砧板上,用刀背將黃瓜拍碎,佐以蒜泥、醬油、鹽、糖和醋。上海人不常喫蒜,這蒜泥黃瓜算是相當稀有的一道蒜泥菜。還有更簡單的做法,是挑嫩的黃瓜、切成片,用麻油、米醋和糖拌食。 日前,高中同學在南京路上的新鎮江飯店聚會,席間,有一道冷拌黃瓜很奇,如麵餅般厚薄,半個手掌般大小,湯水是乳白色的,漂著淡淡的辣油花,喫口爽脆,極是誘人。那天並不是我點的菜,不知道叫什麼,因其極薄,便戲取了一個「蟬翼黃瓜」的名。 這「蟬翼黃瓜」別有風味,著實好喫,回家便試做。挑筆直的黃瓜,去頭切尾後,分成手指長的三至四段,將黃瓜直地對著自己橫放在砧板上,用左手的手掌摁住黃瓜段,右手拿刀,與砧板平行,刀面幾乎帖著砧板進刀,將刀一點一點地從右往左推,左手緊緊摁住黃瓜段,隨著進刀將黃瓜段向左滾,其間不斷調整刀的角度,才能保證批出的黃瓜片厚薄一致。這樣批出的黃瓜會變成一條長長的一片,剩下當中一段圓圓的籽,就不要了。 新鎮江的黃瓜是未經鹽醃的,在我嘗試的過程中發現,如果先用細鹽醃製,不但可以去除生澀的感覺,而且可以把黃瓜片醃成透明的。黃瓜經鹽會變得極其爽脆,說來奇怪,特別是對於這種切法的黃瓜,鹽醃之後還會有一種幼滑的感覺。先將長長的黃瓜片條,切成半指寬的小片,撒入細鹽,鹽不妨多放一點,一會兒還要洗去。將黃瓜拌了鹽後,靜置半個小時,用涼開水洗淨,然後用麻油、米醋、花生醬、芝麻醬和糖用水拌勻,如果喜歡喫辣的,還可以放上一點辣油,但是不要太多,否則會有喧賓奪主之感。 上桌前,用筷子挾出黃瓜,整齊碼放,黃瓜皮和黃瓜片要錯開,絕不可一堆黃瓜零零亂亂地裝盆,再好的東西,沒了賣相,也要大打折扣。 涼拌黃瓜中,最難做的就是這道蟬翼黃瓜了,然而最好喫的,也是這道。市面上還有專門的工具,用來製作蟬翼黃瓜,那東西有點象削蘋果的機器,中間有支針,邊上的刀片靠彈簧倚住黃瓜,厚薄可以通過彈簧調節,手柄一轉,就能切出一條長長的黃瓜片來。其實家庭製作也不必去買專用的機器,所謂熟能生巧,多練練就是了,即使是專業的廚師,也是從批冬瓜、批黃瓜,練成一身好功夫呢。 那天喫飯,席上有我的老師們,還有我的同學們,她們也成了老師,再加上我的妻子女兒,我開玩笑說,這些女人們都是可以管教我的人啊,整個一桌,就屬我最沒地位了!這當然是題外話了。
這幾天網上熱鬧得緊,原因是出了一部《反虐待動物法(徵求意見稿)》,其中有專家建議「食用犬貓肉的,將處5000元以下罰款並處15日以下拘留」,於是引起了軒然大波。支持者與反對者大打筆仗,網上網下鬧得「不亦樂乎」。 「吃狗肉」,最有名的要數劉邦了。我們都知道,劉邦就是個流氓,據說他還在道上混的時候,常去另一個小流氓那兒吃白食,那個小流氓就是樊噲。這個樊噲可不得了,就是衝進鴻門宴救劉邦的那個「頭髮上指,目訾盡裂」,能夠「生吃野豬肩」的壯士,成語「彘肩鬥酒」說的就是他。 當樊噲還是小流氓時,以「屠狗」為生,就是殺狗、燒狗、賣狗肉,而劉邦呢,是大流氓,大流氓當然吃定小流氓,劉邦就天天去吃樊噲的狗肉,不給錢,白吃。 小流氓是不能和大流氓翻臉的,所以樊噲只能逃,帶著狗肉逃到河的對面去賣。劉邦很牛,一見樊噲跑掉了,就追到河邊,居然被他找到一隻大龜,就騎著過了河,繼續白吃樊噲的狗肉。 就像現在的小流氓會劃傷大流氓的BMW一樣,樊噲趁劉邦不在的時候,直接就把那隻大龜給幹掉了。小流氓也真夠心狠手辣的,為了毀屍滅跡,乾脆就把大龜扔到狗肉鍋裡一起煮了。結果沒想到,煮出來的狗肉鮮香無比,一下子就搞成名牌了。 劉邦呢,大流氓的交通工具被幹掉了,但為了輛車去耿耿於懷就不像大流氓了,只是把小流氓的作案工具——刀給繳了。於是樊噲沒法切狗肉了,逼得小流氓只能用手撕狗肉來賣,沒想到,肉的口感更好了。 沛縣黿汁狗肉就是這麼「發明」出來的。待劉邦後來打天下時,樊噲就跟著他;待劉邦做了皇帝之後,還有吃狗肉而作《大風歌》的著名故事。 流氓們大多很講義氣,特別是在大流氓的「幫助」下,小流氓創出了自己的品牌,為了「報恩」,樊噲後來就追隨劉邦打天下,還救了劉邦,於是就有了一句話,叫做「仗義每多屠狗輩」。 當然,傳說歸傳說,笑話歸笑話,其實,劉邦既然沒收了樊噲的刀,讓他切不了肉,那麼小流氓又是如何殺狗的呢?則不能深究了。 其實,吃貓食狗並不能抬到「虐待動物」的高度。沛縣,就是大小流氓的故鄉,食用狗肉的習俗一直流傳到現在。當地在肉用狗的飼養、屠宰、調弄、烹煮以及保存和銷售上,都有了系統化的規模。每年的狗肉相關產值達到十億元人民幣,相關從業人員達到十萬人,並且遠銷俄羅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甚至還榮登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其實,中國各地,食狗者眾,貴州的花江、南京溧水的石湫、廣東的湛江、吉林的延吉等地,均以狗肉聞名,而越南、韓國等國,也都普遍食用,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就一直說,如果有樣東西,你從來沒見過,別人吃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怪。打個比方說,山裡的人從來沒見過蝦,第一次見到有人吃蝦豈不是很震驚,那玩意,長著長長的須,還有那麼多的腳,儼然是個怪物嘛。可海邊的人哪會有這種想法,在雲南,我見識過蟲宴,長短各色都有,當地人吃得不亦樂乎,在別處人眼裡豈不也是「異數」? 南方人吃龍蝨吃蛇,北方人吃蟬蛹,都是很普通的事。但是換位來看,就有人覺得恐怖了。其實,在食物方面,大家應該用平常心來對待,食物均衡,不挑食不浪費,就可以了。 其實,上海人是沒有資格對吃貓食狗說三道四的,我問過好幾個「反虐食貓狗人士」,問他們「醉蟹戕蝦吃不吃」,回答當然是「吃」! 喜歡吃大閘蟹的上海人,嚴格地說,壓根就逃不了「虐食」,因為「眾所周知」,死蟹是不能吃的,要麼活活蒸熟了吃,要麼活活醉醃了吃,反正在動物保護主義者眼裡,都不算「好死」。 上海人的食物中,還有更厲害的。吃生魚片厲害,吃貓吃狗吃蛇厲害,吃蟲吃蛹厲害,但都沒有上海的戕蝦厲害。上海的戕蝦是「活」吃的! 於此,要說明兩件事。首先,戕蝦其實不是上海獨有,江浙兩地均有,蘇州人認為是蘇州名菜,揚州人認為是揚州的。唐代劉恂的《嶺表錄異》寫道:「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綽菜蘭香蓼等,用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以生菜,然以熱飲復其上,就口跑之,亦有跳出醋碟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為異饌也。」從這裡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至少一千多年前的廣州一帶,就有這種吃法。 然後,是這個「戕」字。我們先從吃法說起。這道菜上桌的時候,是一個有蓋的容器:簡陋的,是一個大碗上覆著一隻盆子;考究的,是小瓷砂鍋;新式的,是透明的玻璃燒鍋,小小的一鍋。 如今在飯店裡點這道菜,往往就是用玻璃燒鍋,端上來的時候,可以看到裡面大約盛了半鍋的蝦,約莫二三兩的蝦,一半被浸在湯汁裡,還都活蹦亂跳的。 吃這玩意有講究,需要事先看準一隻鮮活的蝦,將蓋子掀開少許,把筷子伸進去夾住活蝦,輕輕地拿出來,快速地放在嘴中,閉上嘴。這時,神奇的感覺就來了。先是一陣蒜香,伴著酸酸甜甜的味道,那蝦會在你的舌尖跳動,更有種酥酥麻麻的感覺。 吃這種蝦,要吃一個,掀一次蓋子,夾一個,再蓋上一次蓋子。如果哪位朋友好心將蓋子拿在一邊,肯定會被譏笑為「洋盤」。那樣的話,蝦很可能跳出來,帶著汁水四處飛濺。然而,即使再小心,也有著了道的時候,有時那蝦會在筷尖突然跳起來,醬汁會甩你一臉,於是闔桌笑了起來,氣氛便也越發地活躍起來。 這個菜,在上海的飯店裡,寫法多多,有寫「熗蝦」和「嗆蝦」,也有寫作「槍蝦」的,甚至還有「搶蝦」。 「熗」,其實是個常用的烹調術語,指的是「將菜餚放在沸水中或熱油中略煮後取出加作料拌」,上海話中並沒有這個字,上海話中相同的動作謂之「汆」。 「嗆」是個多音字,發平聲的時候指「水或食物進入氣管引起不適或咳嗽」,顯然也不符合。 至於「槍」和「搶」,也是由於音似而用的,而真正的字,應該是「戕」。 「戕」字大家平時用得不多,它的右邊是個「戈」字,「戈」是兵器,左邊是「爿」,就是反過來的「片」,被兵器割成一片片,當然就是「殺」啦。那蝦都被端上了桌,等著現殺,故名「戕蝦」。 有人說「戕蝦」就是「醉蝦」,其實不然。朱彝尊的《食憲鴻秘》中收錄有「醉蝦」一則如下:「鮮蝦揀淨,入瓶,椒、薑末拌勻,用好酒燉滾潑過,食時加鹽醬。」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出,醉蝦的容器是小口的「瓶」,便於貯存而不易污染;其次,這種醉蝦吃的時候並不是活的,因為已用「燉滾的酒」潑過了;最後,醉蝦不是現做現吃的,否則就是「加鹽醬而食」,而不是「食時加鹽醬」了。 前面的半篇寫完後幾天,又見報導說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並沒有完全銷毀,如今又在市面上出現了。一個國家,如果連小孩子小寶寶的生命都可以漠視,還要禁食貓狗,那根本就是滑天下之大 稽。 吃點戕蝦,完全不必忸怩。要用活蝦做,還要新鮮的活蝦。既然都是活蝦,還有新鮮不新鮮的?當然,新鮮的活蝦活蹦亂跳。不要以為一大盆蝦放在那裡,時不時地從水中蹦一個出來的蝦新鮮,蝦之所以會蹦出來,那是因為水中的氧氣不夠,它才會努力地往上蹦。…

你好!
祝賀出書!
自詡老饕,多交流。
王沛仁老饕說吃: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2342824_5_1.html
你好!
祝賀出書!
自詡老饕,多交流。
王沛仁老饕說吃: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2342824_5_1.html